贫贱与哀怨
◎ 朱庆和
先说说我自己。
早晨起来,我把床脚边的小尿罐提到院子的南墙跟,那儿放着一个大尿罐。夜里我尿了三泡,春燕尿了一泡,有些份量。我把小尿罐里的尿倒到大尿罐里,瀑布一样,还闪着光,没过一会儿,大尿罐就满了,上面积了一层泡沫,像刚开了瓶的啤酒。
我呼了一口气,白色的,一下子就散掉了,随之我缩了缩身子。能看见呼出的白气,说明冬天来了,等到河里结了冰,那就已经很冷了。我这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个傻子?其实,我只是耳朵不好使而已。在村里人看来,只要你有一窍不管用,他们就会把你当成傻子,有事没事拿你开玩笑。当着我的面,他们就叫我“聋子”、“大尿灌子”,我知道的。
做好早饭,我先盛了吃,然后喊春燕起来吃。春燕在被窝里跟个虫子似的,动了动。我冲被窝说了声,待会起来吃啊,要是凉了就热一热。我看见虫子又动了动。刚结婚那阵,我总是把热腾腾的饭端到床头,现在春燕不叫我这么干了。
扁担的一头是大尿罐,另一头是腊条筐,筐子里压了块石头,我挑起来朝门外走。路上没几个人,天一冷,都躲在被窝里不出头。只有吴喜贵,他看见我,冲着我说了句什么,我点点头。就是他,曾对我说,你攒足两罐子再挑到地里去不好吗?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你傻啊,挑着块石头来来回回的,不是白费力气嘛!这狗东西,在考验我的智力。但我知道,这不是智力问题,我一罐一罐地挑到地里去,只是想叫麦子早点喝上尿,早点发力,他懂个屁!我就回答他,我有的是力气,你管呢。
挑这种担子,要掌握好平衡,步子要稳当,否则尿就会撒出来。我挑了有些年头了,有经验,没撒过几滴。但也有使坏的,趁我不注意,朝我身后的尿罐里投石子,这样尿就溅到了我身上。我只好掉个头,尿罐在前,筐子在后。但他们继续使坏,朝我身后的筐子里加砖块,可这难不倒我,前面使把力就又恢复了平衡。
空旷的麦地里只有我一个人,麦苗上都打了霜,等我拿尿浇完麦苗,太阳也升高了许多。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一点不假,我家的麦苗看起来很茁壮。我的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长不好才怪呢。老二进了城,老三在罚牢役,他们的地也都给我种了,东一块、西一块,有两三亩的样子,一年到头我干得很累,但当我把一袋袋的粮食扛回家,就觉得再累也值得了。我本想把母亲的地也揽过来种,春燕跟我闹了几次后,母亲还是自己去种了。每当我看到母亲在地里弯腰驼背的样子,心里就难过。母亲对我说,她是劳碌的命,一闲下来就得死。她的意思是,叫我别难过。
前些年,总有人偷挖麦苗回家喂兔子,并以此发家致富,所以我经常到麦地转一转,以防人家来偷。现在没人这么干了,他们都跟兔子一样,红着眼,窜出去挣钱去了。但我还是喜欢站在麦地里,一站就是大半天。别以为我在想什么心事,要说想的话,大概是想快点来场雪吧,好让麦苗盖上被子,舒舒服服地过冬。
站得我鼻涕都流下来了,于是我把它擤掉,甩到了翠绿的麦苗上,我看见它继续朝下流。不去管它了。我开始沿着地头朝前走,经过水泥桥,桥下是几近枯干的河底,继续朝前走,我来到了大坟子窝。村里人死了,都埋在这儿,有的竖块碑,多数则拱一个坟包了事。我爹的坟头也在这儿,还有我爷爷的、奶奶的,老四的坟头离我爹有一段距离,坟堆也要小得多。他们所处的位置没什么标记,但我眯着眼都能找出来。于是我真的把眼睛闭起来,结果顺利地找到了老四。我看见他的坟头上长了一些荒草,已经干枯,看上去像是他很久没剃头了。我把草拔下来,太阳暖融融的,照在老四光洁的前额上。我坐了一会儿,然后去看我爹。他的坟顶上也是,荒草一把。我如数地薅下来,因为坟头大,竟聚成了一堆。我掏出火机把火点燃了。
突然,一个人影挡住了我,在此之前,我似乎听到有人在喊,哪个狗日的在放火。我没理他,继续烤我的火。接着,我看见刘建军出现在我面前,怒气冲冲。
我对他说,一块烤烤吧,天挺冷的。说完,我拿小树枝把火拨得更旺一些。我之所以这么平静,是因为他打不过我,我们干过几次,不管是赤手空拳,还是抄家伙,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他蹲下来,对我说,熄了吧,我的桃树都给你烤死了。这个坟子窝前两年叫他承包了,栽上了桃树,密密麻麻的。
我听了很不高兴,反问他,你把桃树栽这么密要死啊,搞得我清明过年给我爹烧刀纸都没地方烧。说着,我站了起来,一个桃树枝子刮住了我的衣领,我伸手把它折断了。
他很快变得和缓下来,脸上转怒为笑,嘴里不知在嘟囔什么。
我对他说,等过了年,我也栽棵桃树。
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就问他,你是不是不愿意?
他说,这是我承包的地,你在哪个地方栽?这你可得要讲道理,是不是?
他要跟我讲道理,于是我说,你承包的怎么啦,我把它栽在我爹的坟顶上,这个不算不讲道理吧?
栽在你爹的坟顶上,他说,这个我没话说。但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可你不能栽桃树。
我问他,为什么?
你想啊,你摘了桃子,是我树上的还是你树上的,说不清楚是不是?
似乎有些道理,我再问他,那你说栽什么树好呢?
苹果树,他兴奋地说,我记得你爹喜欢吃苹果,你把苹果树栽到你爹坟顶上,他肯定高兴,他要是渴了,摘下来就吃,多方便呢,你说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爹喜欢吃苹果?
你爹喜欢吃苹果,村里人哪个不知道?
我说,好吧,就这么说定了,过了年我就来栽。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我很满意。别以为我在跟刘建军开玩笑,本来是想开一下玩笑的,但现在已经不是玩笑了,成真的了,过了年我就买棵苹果树苗栽上。我抽完他递给我的烟,觉得时间不早了,就准备回家去。走了几步,我突然记起来,尿罐、扁担还在麦地里呢。回到麦地,我挑了空尿罐朝家走。
快到村口时,看见五六个闲人站着,一律黑颜色的衣服,跟乌鸦似的,他们在聊着什么。村头又有一大块地给圈了起来,说是要盖工厂,生产汽车轮胎。看见他们在那儿指指点点,我想他们的话题大概跟汽车轮胎有关。待我走近了,他们的目光却转向我,问了我一句什么话,而且都在笑,搞得我很不舒服。我就冲他们点点头,回答说,我去浇了一趟麦。但他们还是紧盯着我不放,还笑得更厉害了。有一个呲着牙对我说,聋子你快看看,你的尿罐子都碎了。我不相信他的话,他就把牙呲得更厉害些对我说,谁骗你谁是你儿子。看他的表情是认真的,他们不敢跟我开玩笑,因为都尝过跟我开玩笑的厉害。我就回头看了看,果然尿罐已经碎了,只留着两个破锣似的残片挂在扁担钩上。我笑了笑,说,没事,碎就碎了吧。
我怕春燕说我,就把碎尿罐丢在了路边。回到家,却没看到春燕,锅里的稀饭也没动,冷冷的,像是结了冰。我喊了几声,春燕还没出现,大概她又跑到谁家玩去了。我站在屋檐下,想到了尿罐的事。路上没细想,现在我要好好捋一下。从麦地里回来,尿罐好好的,怎么就碎了呢?我记得挑着空尿罐从麦地到村口这一段没碰见任何人。难道是村口那几个人趁我不注意,拿石子把尿罐打碎了?但当时我看了看身后,没有碎片。难道是早上出门时,吴喜贵搞的鬼?如果是那样,我也不会把尿浇到地里去了。显然这个说法不成立。想得我脑浆子疼。
我把稀饭热了热,吃了,吃完饭到床上睡了一觉。我有午睡的习惯。醒来的时候,感觉外面起风了,小北风在房顶上吹着口哨,虽然我没听到口哨的声音。我不再想尿罐的事了,也不值几个钱,明天去镇上买一个。
下午去了趟藕塘,在路上我又碰见了刘建军。他的出现,让我突然明白,一定是他下的手,没错,他对我要栽苹果树的事怀恨在心,于是尾随在我身后,把尿罐给打碎了。我拦住他,问道,是不是你打碎了我的尿罐子?他辩解说,我神经病啊,去打碎那破尿罐子。北风吹得他眼睛眯了起来,我看不到他的眼神是否在躲闪。我当然不信,就问他,不是你打的,那我为什么又碰见你了呢?他被问得莫名其妙,一时不知怎么应对。但他还是回答了我,老五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可能叫我天天躲着你走吧?看着他无奈又无辜的表情,可以判断,尿罐确实不是他打碎的。
藕塘本来是一块低洼地,靠近河边,种什么淹什么,养鱼又太浅,没人承包,几乎成了荒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信息,就去了一趟南乡,回家后以很低的价格把洼地承包下来,搞起了藕塘。头年因管理不善,藕都烂在了泥里,但从第二年起开始赚钱,一年有两三千块钱的进账。
我从藕塘挖了四块藕,挖藕的感觉真好,像是把孩子从娘胎里抱出来,小心翼翼的,不能伤着,洗干净后,细胳膊细腿,白白嫩嫩。在我洗藕的时候,看见陈有光从岸上经过,我把他喊住了。我本来想问他,老婆找到了吗?但没这样问,我觉得不应该跟他开玩笑。他站住了,以为我要分他两块藕,可我没那个意思,喊住他只是随便问他一句,这么急着去干什么。他停下来,一转身,刚好北风迎向他,把他的头发吹了起来。他指了指蓬乱的头发,没说话,但我明白了,他要到镇上去剃头。我说,天还要冷的,留着暖和,剃他干嘛呀?他大声地回答我说,我剃头去死。说完,又急匆匆地走了。他这人可真有意思,大概是因为我没分他两块藕,在跟我说气话。陈有光患羊角疯,家族遗传,说不到老婆,曾经跟老大很要好,但自从老大倒插门到常庄去,他就没什么朋友了。其实他有过老婆,是个傻子,丢一回找回来,丢一回找回来,又一次丢了就再没找回来过。
晚饭我炒醋溜藕片,炒好了拿碟子反扣着,等春燕回来一起吃。上黑影的时候,我母亲先来了,她带了七八个馒头,刚蒸好的,还冒着热气。她应该清楚我从不吃馒头,还带来干什么呢,她肯定是老糊涂了。
我和母亲一起看电视,但屏幕不清楚,雪花子直落,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听电视说。母亲从不挑节目,我看什么她就看什么。我侧头望望母亲,发现她在打盹。我对她说,你回家吧,天黑了路不好走,又刮风。她立即醒了过来,说,等春燕回来就走。她是怕我跟春燕吵架,这我知道。她曾经把那句老话挂在嘴边,“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这话意思是说,媳妇要经常打,她才能听话,这是说给做丈夫的训世良言。但母亲却对我说,小五你可别打春燕,要疼她,知道吗?母亲叫我快点催她生个孩子,好拢住她的心。我和春燕结婚五年了,没个孩子,母亲很忧虑。她不止一次地叹息,说我种庄稼栽藕都是一把好手,可怎么就在春燕肚子里下不了种呢?我答应母亲说,等过了年,我和春燕就下种。
春燕回来了,我看见她就把电视声音关小了,但她还嫌太吵,我就不得不继续关,一直到我听不见为止。我对春燕说,吃饭吧,醋溜藕片,我刚炒的。她眼一斜,说,吃过了。那我只好继续看电视,我还不是太饿。我瞄了瞄春燕,看见她也在看电视,但似乎又不在看,只是在盯着电视生气。电视画面突然模糊一片,大概是春燕刚才进门时风太大,天线动了一下的缘故。这个破电视就这样,太娇气。这是一台黑白电视,结婚那年买的,现在村里人都看起了彩电,装了有线,能收一百多个台。收那么多台干嘛呢?又不能当饭吃。我的意思是,人过得不能太奢侈了。我起身调了一下室内天线,没调好,就到门外调室外天线,我左右转了几下,接着回屋继续调。这时,春燕骂了一句,调你妈X啊调。我好像听见了,但没理她,继续调我的。春燕朝后看了一下,似乎刚发现我母亲在,于是又骂了一句,调你妈X啊调。这次我真的听见了,她在骂我的同时,还骂了我母亲。我看看母亲,她好像没什么反应。
我调好了台,继续看电视,体育频道,一个水上芭蕾节目。多美的舞姿啊,无声的雪花落在水面上,我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春燕说,怎么尿汁子都掉下来了,一个洗澡的节目就这么感人?母亲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流泪。春燕上前换了个台。我非常生气,顺手拿起馒头朝她身上砸去,春燕也不示弱,准确地接住了,然后朝我还击。一时间,母亲身陷在馒头的枪林弹雨之中而不知所措,她狠命地跺脚,嘴里骂着,作死,作死。
母亲临走前把那些馒头捡了起来,母亲走后又被春燕一脚踢翻,七零八落地滚了一地,我们谁也没去捡。我把小尿罐从南墙跟提进屋,便躺到了床上。我记得刚结婚那阵,我和春燕多恩爱啊,我看着她白嫩嫩的身子,说,我真想把你吃掉。她攥住我的胡萝卜,说,还是我吃你吧。说完,我们就搂在一起睡觉,一天睡到晚。不睡觉的时候,我给她铰指甲,她给我掏耳朵。现在我们还睡在同一张床上,但一人一个被筒。我感到有些累,很快就睡着了。中间,我醒了一次,撒了泡尿,春燕被尿声吵醒,气愤地说,操你妈X的怎么还在尿,是不是打算要尿到天亮啊?我很羞愧,但同时以为她原谅了我,就抖了抖下身,钻到她被窝去,结果被她一脚蹬了出来。
再躺下来,我却睡得很浅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春燕在动,但不是一个人,好像是两个。老二没进城的时候,春燕经常朝他家跑,想勾老二。老二有一次对我说,春燕这人不老实,要看住她。而现在她居然把男人勾到了家里,还就在我眼皮底下。我虽然耳朵不好使,可我的眼睛没瞎,看得分明。别人把我当傻子,春燕也把我当傻子,这是我不能容忍的。于是我把一生的力气都集中在了右脚上,狠狠地朝春燕磴过去,滚你娘的X!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春燕不在床上,我想她可能跟别人跑了。我做好早饭,吃完后打算去镇上买个罐子。路上,我听村里人说,陈有光昨天剃头时死掉了。怎么死的?说是他想抄近路,就从麦地斜插过去,结果被刮下来的电线过死了。我听了之后不打算去镇上买罐子了,就返回去,躺到床上,我要等春燕回家。我空等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春燕还没回家。看来,我的想法终于得到了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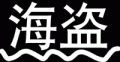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朱庆和,
1973年生于山东临沂,毕业于东南大学。现居南京。在《他们》、《橡皮》、《芙蓉》等发表诗和小说,并有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系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著有小说集《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