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去不了西藏
◎ 曾骞
我想去西藏已经想五年了,今年我二十二岁,想去西藏那年,我才那么小,那个时候,我连台相机也没有,而现在我也一样没有相机,一样的事情有很多,其中还有我依然没去成西藏。
有一年,我碰到一个叫彭弢的青年,他是我的老乡(广西人)。他那时和我现在一般大,但已经自费去了三次西藏和一次尼泊尔,出过两本关于西藏的游记。这让我很羡慕。他对我说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全部的盘缠只有六百块,还说整个旅行的过程就像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轮回。我没去过西藏,不知道六百块到底是多是少,但我坐过火车,知道六百块对于一次长途旅行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觉得有点不靠谱。但我无法想象,这个青年在那个高原上是怎样地一路跋山涉水的。我还想象自己是怎样在那个高原上游走的,我想着自己开着JEEP,最后还修成了密宗。所以我也有点不靠谱。
我经常面对着北京那尘土飞扬的天,而不知所措。我时常期待着,能发现一种能够使人保持持久欢乐的办法。没有乐趣的生活令人生厌和恐惧。乐趣的转瞬即逝则令人怀疑乐趣的本身。我每天,每刻都在怀疑着自己本身。我被失望的情绪所困扰着,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感到失望。致命的是,生活里缺少激动人心而又神奇的感受,哪怕是它们突然地、短暂地出现的时刻也没有。没有灵光。
当年德国纳粹派了盖世太保去西藏寻找大祭祀,虽然没有所获,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表明了一种信仰。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经常问自己,问自己我的信仰是什么?其实问了也没用,一样地会感到困惑。困惑之后就是自恋、自卑、自摸、自慰,我不上班,每天只干这四件事。有个事实是,我不了解世界,因此而自恋,我自恋了必然自卑,我独自一人,所以必然自摸也自慰。
信仰和信仰什么完全是两码事儿,我现在没有信仰也不信仰什么。我从来都不认为信仰的缺失会造成人心的迷失。我也更不愿意去想,信仰的缺失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没有能力去关心那么大的范畴。我只是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失去了信心,因为精神月经来得太过频繁。那种感觉就只是一种空,你觉得空,一切都只是空的,你也唤不起记忆来,也没有了憧憬。只是在死气沉沉中捱日子。
那么多的人去西藏都冲着精神二字。假如西藏真能解决那么多的精神问题,那么我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多到总是在压抑我们的心,重到让人感到心已非心而只是被换填了一块石头。我觉得,在那片高原上,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关系,一种自身与世界间的关系,那种关系便是所谓精神的全部。或者,也许只是一颗充满了能够导致极乐的慈悲心而已。或者,这一切既是:光明、无垢、空、狂喜、大乐、万宗归一。
我自感到心头心魔太重,还觉得自己有点居心不良,我更愿意相信自己有着一定的异教天分,所以我更愿意去关心那些和西藏有关的密闻和传奇。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可悲,因为我确实感到了自己的不纯粹。但不管怎样,我始终认为西藏和佛是不可分的,和禅是不可分的,这一切都只和内心有关,可能我还会想到命运,别人、或者就是你,你还会想到你的命运,想到精神那两个字。
我还想到那六百块的事,我除了有点羡慕外,还有点胆怯,我在想那是怎样的一条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还想到一段话:
然而,禅是严厉的,远不是简单易行的。这是一条通向一片高耸入云的几乎是垂直悬崖峭壁的道路,其弟子、信徒们必须放弃绳索和钉钩。那些经过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坚持不懈、艰苦努力之后完全有能力进入其中的人会突然间出现在耀眼的大雪中,并完全从上面怀着惊奇的心情观察下部那些他们过去认为是宇宙的狭隘山谷。
——《西藏佛教密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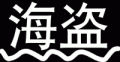 ┩目录┡ 曾骞,1984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暂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