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 乌青
夏天的午后,阳光很亮,我从家里出门去找周勇。走出巷子,走过环城北路,经过张建华家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抬头看看,经过北门桥,也许我会在桥边看一看泛着光的河面,走过北大街,走过十字街,继续往前,走过南大街,走过南兴街,然后向左拐,再走一段路,就看到周勇家了,他家开了个小卖部,这时候没有生意,安静,他母亲看到我,说,周勇在路上,然后就喊,勇,勇,乌青来了。我上楼,看见周勇在楼梯口等我,微笑着,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他的妹妹站起来,回自己房间去了。然后我们坐在那里。
我们坐在那里一开始好像没什么可聊的,但过了一会儿就不知道从哪开始聊起来,一直聊到了傍晚。那是我初中和高中的暑假的情景。如果是下午,通常是我去找周勇。而晚饭后,我们则采取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约会方式,见面后就在街上没完没了游荡聊天到深夜,跟踪女孩,如果口袋里有点钱,我们就去冷饮店或者电影院。
在2000年之前,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周勇,那些年,楚镇的人们经常看到我们在街头游荡,楚镇的漂亮姑娘几乎都没我们跟踪过,楚镇的流氓都知道我们俩的口袋里掏不出几个子儿。
根据周勇的说法,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他就去过我还在南兴街的家。那是小学四年级,他说他被林新法带到我家玩。我不记得了。我记得,在五年级,我和林新法打了一架从此不相往来。所以,小学,尽管我们在一个学校,但我和周勇并不认识,至少我不认识他,那时候我主要和张建华玩。初一,我和周勇也在一个学校,但我们依然不认识。到了初二,我们在一个班了,可似乎我们还是不认识。
有一天中午,我特别早的来到学校,上了楼,看见周勇一个人站在教室外面的阳台上。我从他身边走过去,走进教室,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我也站在阳台上,周勇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他。一开始我们好像没什么可聊的,但过了一会儿就不知道从哪开始聊起来,一直聊到了上课铃响。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拼命怂恿我的同桌跟周勇换位子,但这个外号叫敢死队队长的家伙死活不干。
此后每天早上,我们5点钟就起床,约了去爬山,然后下山吃早饭,然后去上学,放学以后也不再安分回家,而是去郊外河边停着的船上或者田野里或者丫鬓山脚下的竹林或者西青山那条上小学必经的路上每天聊啊聊,聊到不得不回家的时间才找一个离双方家距离差不多的中点分手。周末更是一整天都到海边或者乡村瞎逛甚至骑车去另一个镇子,那些日子真是非常美好。
我们一起搞“金属眼镜侦探社”一起搞“文瘾文学社”;一起躺在收割的田野里谈论学校的女生;一起夜里飚自行车;一起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交战”;一起在集市的时在候去看新鲜东西。一起度过了我们的少年时光。
后来周勇考了浙江工业大学去杭州上学了,后来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我到了杭州去找周勇,两人又开始在杭州街头游荡、跟踪女孩和看电影。很快我被找来的父母抓了回去,但不久我又离家出走了,为了不让我父母抓到,我没有去找周勇,但当我口袋空空的时候,又到杭州找周勇,周勇说,我们一起去绍兴玩吧。那次绍兴之行太愉快了,我们一起去了咸亨酒店喝的烂醉,去鲁迅故居,去鲁迅电影院,去坐乌篷船,去溜冰。然后口袋空空的回去。周勇跟同学接了钱给我买了回家的车票。
再后来,我复读也考到了杭州的一个破大学,但周勇却得了肝炎休学回家了。再后来我辍学了到处游荡,周勇又回学校,然后毕业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去年听我妈说,周勇的父亲自杀了,他母亲就举家搬迁,不知道哪去了。
我想,一些时候,周勇一定会想起我,就像我经常想起他一样。比如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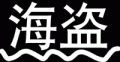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