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Let`s Play之后
◎ 向阳花
能够与音乐再次重逢,应当感谢我那把生了锈的贝斯。我想就先从我的贝斯谈起。她的名字叫FENDER,出生在墨西哥,长大后被一个伦敦佬以六百英磅的价钱买回去玩耍。后来这个伦敦佬一时想不开,跑到了中国北方一所三流大学当外籍教师,结果搞得自己在经济上狼狈不堪,因此我和FENDER才有幸成了知己。
认识FENDER之前,我是与一位国产贝斯相依为命的。她的体重不亚于我,以至于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都如同抱着一位彪捍的女友跳了一支令人吃力的舞,而抚按弹拨她的感觉更加不堪回首,发出的尽足是索然无味的声音,让人戚然。与FENDER在一起却全没有这种痛苦的体验。相反,抱着它是一种幸福,一种两相依靠的温暖。亲爱的观众,你能体会和明白吗?不妨试试搂搂你身边的爱人。所谓默契,无非是情感上的对位与合拍,不管对方是人还是琴。这实在扯远了,还是长话短说,直接谈这一次的音乐演出吧。
真没想到,再次鼓捣音乐是玩即兴,与LZ和AB组成了“郑伯伯”玩票式组合,而且打算操弄实验噪声。这对于像我这种摇滚未遂多次的音乐半吊子青年来讲,纯属如同操着十六种腔调满世界告诉别人说自己会讲十六国语言,韩国人面前说越南语,越南人面前说韩语,大抵如此。反正在深圳这个地方,真正能听懂实验音乐的人凤毛麟角,对于我来说,不怕丢丑在先,敢于大胆尝试,自然无所畏惧。当晚来看演出的观众很多,不少是来凑热闹的,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偶尔会有人捂住自己的耳朵,但全都坚持听到了最后。其中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的音乐略有赞赏,真有些受宠若惊。“郑伯伯”演出之后,有人站到我身边问我,“你们的音乐是想表达什么?”我当时吹牛说,“我们三个人在用音乐进行心灵上的对话。”眼见那位朋友的脸色立刻变得高深,我接着胡说八道,“LZ用他的电脑搞出像肚子在咕咕叫的声音说他饿了,AB拿出一个碗来又敲又磨地问演出之后一起去哪里吃饭,我则在四根弦的贝斯上挨根敲打了一遍,意思是回答他们去梅林四村大排档。”那位朋友大笑,我心想,音乐如果能这样简单便好了。他人又岂知创作中的诸多困惑与巧合呢?除了传达给他们乐趣之外,我无法解答。
但话说回来,玩归玩,做音乐还是要相当重视的。我们前后共排练了两次,从毫无头绪到想法产生,先是确立了音乐结构与感觉,再是用独辟蹊径的方式去演奏,其过程有必然也有偶然。应该说是LZ的声场和AB的人声与謦击让我找到了对音乐的感觉,自此我从站在音乐之外开始进入到音乐之内。我想到用一些五声音阶去辅佐,能够做出类似古琴的声音则更好。想法应需要以相应地技巧去实现才对。可我技艺空乏,只能靠寻找速成的捷径以期圆满。现在来说说演奏时我用的工具——一把内六角扳手。FENDER接近6年未碰,已是锈迹斑斑,琴弦打品的声音十分严重,本想用扳手调校一下,但有些螺丝基本接近死亡,根本无力可施。索性用扳手打击演奏,却惊喜地发现撬动琴弦发出的共震与磨擦琴弦时的细碎噪声有着很特别的感觉。由于是首次做这样的演出,想尽量玩得简单一些,我没敢做太多的音出来,只是在几个音阶上反复,必然缺少变化,显得过于单调。更欠缺的就是与LZ与AB的配合了。排练了两次我才多少找到一些呼应与配合的感觉,但很不成熟,演出的时候尽管感觉还不错,但因换成了与排练时不同的音响设备,贝斯的音色听起来使我不大舒服,导致好几次搞错了位置。真可谓漏洞百出。看来音乐这东西,还真是不能欺人欺己啊。
总之,我在深圳的首次演出还是比较成功的,中规中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最大的喜悦则是获得了只有创作音乐才能带来的乐趣。我向来不喜欢学院派的教条,能够像“郑伯伯”一样如此自由地玩音乐才是一件快乐的事。突然想起LZ的那张个人EP《Let`s
Play》,就此为题,作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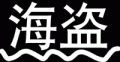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向阳花,男,现居深圳,深圳独立电影社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