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兮,似万物之宗
◎ 贾冬阳
1。
几天前,六回约我为《海盗》第二期的“翻书”栏目写一篇东西。他说,你就介绍一下你正在读的书就行,标准是让我能看懂。我答应了。我正在读的是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一本书,名字叫《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但紧接着我就遇到了困难。最直接的一个是,两周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找到一句合适的话,来开始这篇文章。换句话说,我没感觉。既然这样,我就想用海德格尔在他的另一本书《演讲与论文集》的序言中说过的一句话来开始。他说,“一位作者倘若确是作者的话,或许就没有什么要表达和传达的。他或许甚至也不想刺激什么人,因为受刺激者已经对自己的知识蛮有把握了。一位在思想道路上的作者充其量只能有所指引,而本身不能成为智者意义上的一个智者。”
2。
渊兮,似万物之宗。
我从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借此句为题目。它的意思,即使到本文结尾,也不会有个交代,但或许有所指明。
3。
海德格尔是谁?
据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同维特根斯坦一起,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还在纳粹时期犯过“政治错误”,被很多怀着不同目的的人紧紧咬住不放,但就是不肯道歉或忏悔,因此为学界留下一段“海德格尔的沉默”的公案。1966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开场就说:“他生出来,他工作,他死了。”关于海德格尔的生平,大概也可以这么说。我只想说这么多。德国人萨弗兰斯基写过一本《海德格尔传》,有中译,比很多教科书上对海德格尔只言片语的介绍都详细。
在一些几乎从未读过海德格尔的人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此在中心论者”。那是他们基于对《存在与时间》这本几乎连海德格尔本人都“不在乎”的书的误解。包括一些哲学史家在内,他们草草将《存在与时间》钦定为海德格的“代表作”,然后要么布置成纪念馆,要么投去不屑的目光。
被称为20世纪极其深刻的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几乎终生把海德格尔作为潜在的思想对手,但他在晚年时却说:“我越是思考海德格尔,越是觉得他深不可测。”“我能想象得到的我们时代最大的愚蠢,就是闭着眼睛不读海德格尔。”
没错,《存在与时间》以“此在”为中心所展开的“基本存在论”仍然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结构,尽管其间的“肉身性范畴”非常特别,贴近着人的生存状况。但是,它真是海德格尔要说的和想说的吗?此书最后一节即“第八十三节”:
研究一般存在“观念”的源头与可能性,借助形式逻辑的抽象是不行的,亦即不能没有借以提问与回答的可靠视野。须得寻找一条道路并走上这条道路去照明存在论的基础问题。这条道路是不是唯一的路乃至是不是正确的路,那要待走上以后才能断定。涉及存在阐释的争论不可能得到疏解,因为它还根本没有得到点燃。归根到底,这一争论不可能“自生自长”,倒是要开启这种争论就已需要某种装备。前面的探索就正朝向这唯一目标进行着。它行到何处了?
原来,《存在与时间》不是海德格哲学的“正文”(如“代表作”之类),甚至连“绪论”都不是,仅仅是一个“引言”而已,“存在”观念的源头、基础问题、存在阐释的争论,“根本没有得到点燃”,即便准备性的上路,也还不知行到了何处。
也就是说,“思想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存在与时间》后,海德格尔至少寻找了三种进入“存在”的路向:
——回归希腊语源以唤醒希腊思维聚集的初始经验;
——重新解释西方哲学史作为“路标”(如胡塞尔、尼采、黑格尔、康德、莱布尼兹、司各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拉克西曼德等);
——阐发荷尔德林等诗人的诗与思与在;以及与此参照的“技术追问”。(参阅我的导师张志扬先生《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一文,载“启示与理性”第三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以上作为“背景”。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这本书,就是后期海德格尔反对逻辑主义的或工具主义的语言观,提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理解的集中展现。
4。
什么是语言?
流俗之见认为,语言是人的发生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是对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是对内在观念的一种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现。人们进而把在发生过程中被说出的东西,即符号关系的系统,当作语言的本质要素来研究。在这方面,生理学、物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包括元语言学)等等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关于语言的知识。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表象-对象性思维方式根本触摸不到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反倒把一切语言给形式化和技术化了,使之成为全球性的信息工具。甚至在“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方式中,就注定了语言将在人的追问与研究中扭身而去。注意:“什么是……”或“……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是典型的希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如今已经弥漫为全球性技术思维方式。在这样一种提问中,人们将所追问的“……”固置在“什么”中,总想找出一个确定的“概念”和“定义”来加以把握、算计和利用,从而遗忘了“是”本身。再说得明白点,在此问题形式中,垂直涌断的“逻各斯”躺倒为铺陈连绵的“逻辑学”——活生生的“生成”与“涌现”已经被泛滥的“知识”给遮蔽了——“道隐无名”。引号中的“知识”,有一个古希腊名字,叫“意见”,在巴门尼德眼里,它们属于群氓。
那么,诗人与哲人对语言都说了什么?
“(语言就是)思想与存在的同一。”(巴门尼德)
“唯语言存在,没有语言外的存在。”(唯名论)
“存在即解释。”(尼采)
“语言世界即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斯凡特·格奥尔格)
“(语言是)口之花朵。”(荷尔德林)
“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
“语言是理解了的存在。”(伽达默尔)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
可见,那些“伟大的心灵”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相同的东西,种种分歧无疑要求那些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应该保持审慎与警惕。
需要提示的一点是,这本书共六篇文章,即使全部读完,那些渴望世界观,急需形而上学的人也不会搜寻到任何海德格尔关于(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的确定性回答。就象在《什么召唤思?》里一样,直到文章结尾,海德格尔也没说出究竟是什么在召唤思,他只是在不断的剥离中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恍惚之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
但读了跟没读肯定不一样。或许果真如此,“在我们这个最激发思的时代里,最激发思的,恰恰是我们不会思。”
5。
语言是:语言。
我想单分一节把这句话摆出来。
6。
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他说:
“语言是:语言。”
他清楚的预见到健康的常识理智的反应,“受过逻辑训练的心智能够计算一切,因而最为盛气凌人;它称前面这种话是毫无内容的同义反复。仅仅把同一回事情说上两遍——语言是语言,这如何让我们深入呢?”海德格尔回答说:“我们并不想深入更远的地方。我们惟求仅此一次便达于我们已经居留的所在。”他接着说,“因此我们就要思量:语言本身的情形如何?因此我们就要问: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我们答曰:语言说话。”
语言说话。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人说话么?难道海德格尔要否定人是说话的动物这一由来已久的见识?否定说话是人的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人之为人的特性?插一句:“语言”这一词语已经被形而上学概念性思维方式用滥了,如同“存在”、“真理”一样,几近晦暗不明。对付这种糟蹋与败坏词语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词让给那些糟蹋与败坏它们的人。所以后期海德格尔用“大道与道说”这一词语重新标示他所踏上的思想道路。但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探寻、还原并且激发词语原初的意义与力量。同时基于翻译上的原因,我在这篇文章中始终使用“语言”一词,而将“大道与道说”保留在每个人的阅读中。再插一句:启蒙时代以来,所谓主体性的复活,已经复活到这个地步——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中心。无物不为我役,人类简直已经把地球变成了“行星工厂”。与此同时,人类被技术连根拔起。反过来,被技术连根拔起的人类变本加厉的对物与语言进行疯狂的掠夺与滥用,离弃了原始的“根基”,本真的“家”。插语结束。
海德格尔要问的是:人何以说话?什么是说话?
语言说话是一种命名。这“命名”不是把某种词语贴标签一样贴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上。命名是一种召唤。它邀请物,使物之为物并与被传召的人相关涉。物之物化聚集着天、地、人、神四重整体并使之栖留于自身,于是才有世界的敞开与显现。“纯粹所说乃是诗歌。”
人说话,是因为人应合于语言。这种应合是一种倾听,归属于无声的寂静之音(别忘了,中国古代的老子早就说过:“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因此,“诗人把诗人的天职经验为一种对作为存在之渊源的词语的召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其他任何一首伟大的诗篇都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在此,我们是否可以断言:诗歌不是创造,它与自由无涉,而是一种“听从”。他恢复并激发词语原初的命名力量,并被这种力量带向神秘的虚无。
别以为可以对语言为所欲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占有就占有,想抛弃就抛弃。如果你觉得你占有了语言,那一定是你被语言占有了,语言仍在你之外,成为反讽。在此,转一句张志扬先生的话: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并不理解他的老师何以在三十年代后要中断解释学,从“看”转向“听”,即从“时间”转向“空间”,从“解释”转向“运思”,让语言彻底从“人说语言”的时间境域中挣脱出来,还语言于旷野,人只有在无意义矫饰的旷野之上方可聆听原初的命名与最后的判词。
7。
我的简述到此为止。它远远不够。
它包含了太多的跳跃、抽取与省略,比如语言的“显/隐”二重运作、“存在论差异”、“诗”与“思”、“解蔽”与“聚集”……,它们不是这篇东西所能承受的。所以——
阅读是一种相遇。它要求走向它的人置身其中。
面对神秘的虚无,那不确定的生成之隙,太多的探究与讲述就是太多的误解与迷途,或许唯有沉默的倾听才能走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深渊”乃基础之缺乏,任何试图为其奠基的企图,都是一种僭越,因为人不是神,人的限度注定无论谁都无法完成那“致命的一跳”。我们生活在悖论中。注意:是悖论,而不是矛盾。因此,我在界限的意义上理解语言,它不是“平面”,不是“世界”,不是“存在”,当然更不是“思维的现实性”、“理解或交往的工具”,而永远是可说与不可说、确定与不确定、经验与超验之间的“有-无”与“显-隐”的界限。
2006年5月16日,海甸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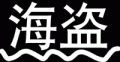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贾冬阳,男,1977年生于吉林,现在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