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街道
◎ 曹寇
我想写写我所置身的街道,红山街道。以前写过次,觉得没写好,所以再写一次。
红山街道位于南京城市东北角,是城外。早前是菜地,城市扩张有必要使这些农民把菜地让出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左右,这里开始建造居民楼,但为数不多。我于1995年左右曾乘坐当年盛行一时的三轮“马自达”来过这里,价格是三块钱,驾驶者是个瘸子,拐棍就摆放在他枯萎的腿边。那时候政府为了使残疾人有个着落,任命他们驾驶这种危险的交通工具流蹿于大街小巷自谋生路。当时,也有些四肢健全的下岗职工也干这事,用以养家糊口,一时三轮马自达像蝗虫一样在城市各个角落泛滥成灾。政府只好取缔,继而抓捕。但他们已练就了高超的驾驶技能,灵活机动,总是出其不意,继而又踪迹全无,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乘坐这种交通工具,我总是选择瘸子,非瘸子不能获得我的信任,似乎惟有瘸子才能给我们带好路,或者说,我对残疾人充满了同情心。其实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没有给我好好带路,或者没有把我送到准确的目的地,那么我就拒付车资,而他们因为腿脚不便,是没法抓到我的,就是这样。
1995年,我不叫曹寇,叫赵西,我哥哥赵东独自一人在红山街道一个面积有五百多平方的大仓库里住着。他一面照看那些由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跃进牌卡车,一面自学英语,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确实如此,对于一个当代青年而言,获得一张相应的文凭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意味着他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娶不到一个模样端正的老婆,以至于生的小孩也很低级。当时赵东已经通过了几门考试,但科目达十四门之多,所以获得文凭的道路还比较漫长,同时也充满了希望。他当时也学会了驾驶,所以他开着车带我去附近一个菜场买大白菜和肉。然后再回来,于仓库一角几十块砖搭就的灶上生火做饭。我们兄弟很喜欢吃肉,但我没想到赵东烧的肉如此好吃。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大白菜烧肉。因为仓库太大,在东边烧锅做饭和到西边撒尿,均不会影响到中间那张床铺。我吃的很香。1995年的红山街道是多么荒凉啊,没有公交车,还保留着大片的菜地,一些被圈出的地枯草丛生,成了赵东和附近建筑工人天然的厕所,新鲜和陈旧的大便像地雷一样遍布其中。其时,若干建成的居民楼还未有人入住,窗口都黑洞洞的。还有那些正在营建的楼房工地,在傍晚,像锈迹斑斑的废墟那样矗立于昏暗之间。天一黑,就什么也没有了。仓库外寒风萧萧,我和赵东一人一头躺在那张破床上抽烟,旁边是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机,上映着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和MTV。那些台词、歌曲至今我仍有记忆并能吟唱。
赵东是羡慕我的,因为我当时在读师范,户口农转非,毕业后国家会分配我一份教师的工作。而他呢,运气不好,没能考上学校,只好自学成才。他跟我说了一些自学考试的事情,说的挺激动的,甚至还读起了教材。this、that的,我毫无兴趣。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买了瓶黑墨水和一只岔了头的破毛笔在仓库的墙壁上随意涂鸦,有“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这样符合驾驶员身份的话。他说,你字好,也写两个。于是,我就操起那只毛笔画了起来。这种书写方式真是太自由了,字的大小、形式和写的内容,随意。那种自由让我感到酣畅淋漓,有如一个须发尽白的老书法家用拖把在庞大的宣纸上拖了点什么那样快活,甚至更快活。在睡觉之前,我们还说到了父亲,那个乡村会计,他同时做好几家厂的账,其收入在当时农村算是不错的。还有母亲,她独自一人在家里种六七亩地,很苦很苦,但她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全家都是幸福的。如果说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我,我对教师生涯已未知先觉地感到了恐惧。
1995年的年底就是这样。新年开始了,1996年元月,我们的父亲突然死去。我和赵东分别从学校和仓库赶往家中奔丧。直挺挺躺在一块门板上的父亲显得那么谦逊和慈爱,甚至还显得深沉和博学。我并没有怎么哭。后来我和赵东两人呆坐在房间里,窗外是村子的石子路,父亲每次回来都会从窗前划过。他骑车姿势总是很僵硬,腰挺得很直,下车的动作也总是显得仓促、不自然。总之,他永远像一个刚刚学会骑车的人那样骑着那辆破破烂烂的二八长征自行车。我们意识到父亲再也不会划过窗口,心里多么悲伤。赵东于是又哭了,我也流泪了,但我尽量不发出声。我想安慰赵东,以后日子就靠我们自己了。可我也没有那么做,他是我哥哥,轮不到我装模作样对他搞什么抚慰,如果抚慰,是不是我该拍拍他因为悲痛而弯曲的脊背?我感到羞愧。
转眼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父亲已在村外那个坟场做了十年的鬼。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已经腐烂,只是一具发黑的骨头了(他是土葬)。我们兄弟只在清明才结伴去给他烧几刀草纸。此时的我们已分别搬离了村子。父亲死后,赵东放弃了自学考试,开始上路,成为一名持B证的驾驶员。然后很快就和他一位女同学结婚了,并且以同样快的速度生下了我的侄子。结婚后,赵东一家就搬离了村子,进到城里,于去年买了房。我的侄子的生活环境已和他的父亲及我没有任何相似点了,他被妈妈送去学画,在幼儿园跟着阿姨唱歌。他也没有见过他的祖父,那个喜欢将手伸进小男孩裤裆摸下小鸡巴的中年男人。他的祖父停留在中年,不是老头。至于我,当然是服从分配去当了教师,然后买了房子。值得说的是,我买的房子就位于红山街道,距离1995年那间仓库的距离大约有八百米。
经过十年的发展,红山街道已完全变了样。这里居民已达十万之众,所有的社区设施一应俱全。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乘坐十几路公交车分别到达南京市的各个角落,然后再由各个角落顺利并精确地回到家中。我是2001年搬来的。已住了五年之久。我已对这里所有的事物熟悉了。无论去哪儿,包括回到村里给父亲上坟,“回家”所指正是红山街道,而决不是村里那几间因久无人居而破败不堪的老房子了。另外,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愿离开红山街道,这里可以购买一切用品,可以去银行取钱,也可以去银行缴纳水电费用。吃饭,如果母亲不在家,我可以去熟悉的一个叫“清雅”的小饭店解决。在“清雅”,老板娘的妹妹曾来帮过几次忙,她很漂亮。或者谈不上漂亮,总之她长得不错,对我很有吸引力。可惜她结过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结婚。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结婚。关于结婚,多年来我参加了无数的婚礼。新郎和新娘站在饭店大堂中央的台子上,接受主持人和亲朋好友的刁难和祝福。他们无不办的很隆重。但据说,所有客人的份子钱足以支付隆重。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怕刁难和祝福的话,也不会吃亏。所以结婚是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红山街道我的家中,和我可能存在的妻子一起劳动,为人类添置一个人口,虽然并不新鲜,但他将有幸被冠以“新生儿”的名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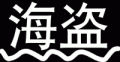 ┩目录┡
曹寇,男,1977。小说作者,现居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