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往事(小说)
◎ 何小竹
在小镇上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蔡小妹比我更年轻。我们的婚姻是别人撮合的。邮政所的所长老卢自告奋勇当的媒人。他跑到蔡小妹家,对蔡小妹的母亲说:“我们邮政所新来了一个年轻人,个儿高,面相好,还是个大学毕业生。”老卢是个胖子,也是个好人。他隐瞒了我的历史: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而受到记过处分,从县邮政局下放到镇邮政所。我其实并不想这么早就结婚。我心里还有幻想。但老卢太热心。他说,成家立业,没有家,何来业?
我是个性欲旺盛的人。蔡小妹身体单薄,结婚不久,就喊吃不消了。她还说,我那个东西太大,让她尤其惧怕。说实话,我是真的心疼她。很多时候,我都只好自己忍着。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忍得住的。我有了忍住的理由:为我的妻子蔡小妹。在县城的时候,我没忍得住,犯了错误,是因为我没有一个要忍的理由。县局的领导对我还是比较惋惜,他们找我谈话说:“其实,你好好的谈个对象,然后名正言顺地结婚,就没这回事了。”言下之意是,你怎么偏偏要去搞一个有夫之妇呢?我很想对他们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是身不由己。但我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鬼才相信。
爱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故事也许会很复杂,但爱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说出来。蔡小妹懂得这一点。她知道我爱她,但她是唯一没有问过一句(“你爱我吗”)的女人。她好像洞察一切,但又似乎对一切都茫然无知。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奔向一个又一个女人,然后又总是不嫌不弃地让我回到她的身边。当然,她也有发怒和悲伤的时候。她也会哭,会闹,会骂人。但一生中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就那么两三次吧。
现在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回忆往事,我真希望她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不要对我那么好。我想,她如果是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我此时想起她的时候就不会这样难过了。我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给她听。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总觉得时间还多的是。我不着急。我要想好了说。我想在说给她听的时候,那些话在表达上更自然一些,朴素一些,轻描淡写一些。尽管我知道,即使我说出来的话晦涩难懂,语无伦次,或者过分地抒情和夸张,她也会一如既往地以微笑来接受的。但是,我已经让她担惊受怕得太多了。我不想在我终于能够向她袒露心迹的时候,还让她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她跟着我受了很多累,吃了不少苦头。但她却认为,是她让我受累,让我吃了苦头了。她经常爱问我的一句话是:“跟我结婚,你不后悔吗?”还有就是:“到这个镇上来,你不后悔吗?”
说实话,我不后悔。那时候年轻,受点处分,从县城到镇上,不觉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生挫折。我还有点喜欢上了乡邮员这个工作。我是学无线电通讯的。在县局,不犯错误的话,过几年我就可以当上工程师。但我更愿意干一份不动脑筋的工作。背着大邮包,骑着自行车,在乡村路上傻乎乎的奔跑,感觉十分轻松、愉快。
每天早上八点过,我到码头上去接县城来的班船。
从县上来的班船靠上趸船之后,就有人喊:“高谷邮政所,接邮件。”一只大邮包就被扔了过来。我接过邮包,并匆匆地在递过来的本子上签字,盖章。然后,将邮包扛在肩上,跟扬师傅他们说声“走了”,这天的第一件工作便算完成了。
我总是比班船到来的时间提前五、六分钟到码头。我坐在趸船上,一边抽着这一天中的第一支烟,一边等班船的到来。趸船上的人跟我都很熟了。我走下江边的那一坡石梯,还没踩上趸船的跳板,他们就开始跟我打招呼。他们都叫我马同志。“马同志来了?吃早没有?”扬师傅端着一大盆面条,站在趸船的甲板上一摇一晃地边走边吃。他身上带有残疾,腿有点跛。但我早就听说,在水里,没有谁比他游得更快,游得更远。他以前是跑船的水手,因为腿受了伤,才转到趸船上。我抽第一支烟的时候,都要给扬师傅装上一支。第一支烟抽完,扬师傅也把他的叶子烟卷一支给我抽。叶子烟的劲头比纸烟大,但我还受得了。扬师傅每次抽我的纸烟,都要说:“这个抽起来没味道,像弄光板婆娘。”有次我问他:“你弄过?”他嘿嘿笑着说:“久走夜路必撞鬼。弄得多了,总要遇上个把个。”这话听上去,有点炫耀,但也不乏一种饱经沧桑的意思在里头。那时候,我涉世不深,对扬师傅这种跑过许多码头的老江湖是怀有一些敬佩的,尽管他每次拿光板打的那个比喻在我听起来并不是十分顺耳。
所谓光板,又叫白虎,民间对阴部无毛的女人的一种称谓。我想到了我的妻子蔡小妹。
那是新婚之夜,闹过了洞房,人们都散了。但她还是把自己抱得紧紧的,不让我脱她的衣服。我猜想她可能还是处女,就开导她说:“不怕的,我轻轻弄。我们是夫妻了,这一关迟早得过的。”她涨红了脸,缩在床角,一声不吭。我又问她:“你妈没跟你说过?”她把脸埋在胸前,说:“说过一下的。”我笑了:“那你还怕什么呢?”但她还是一个劲地摇头。我有点不高兴了。我说:“那你就穿起衣服睡吧,一辈子不脱都可以。”没想到她嗤嗤地笑起来。我问她:“你笑什么笑?”她抬起头来,望着我,脸还是红红的。“我要脱了你不准笑我。”她说。笑你什么呢?我不解地看着她。“好,不笑。”我点了点头,承诺道。“真的不笑?”她又追问一句。我有点烦了,就说:“我要笑了就变成狗。”她看我态度认真而坚决,就微微侧过身去,慢慢地,轻手轻脚地开始脱起了衣服。想那时,我是个什么样的心情?说是火烧火燎一点不夸张。但我还是以极大的耐心等着。我想的是,我是开过眼界的人了,所以我更不能欺负人家。蔡小妹先脱了那件大红夹袄,手便犹疑着,不知道该不该往下面脱。我看着好笑,便打散了一床被子披在她身上,将她裹了起来。我说:“你就这样躲在里面脱,我看不见。”她偷偷笑了一下,就在被子里扭动起身子。这样扭来扭去的,一会一件衣服递出来,一会又一条裤子递了出来。然后,她不动了,只听她轻言轻语的说:“好了。”我心头一喜,一把掀开了被子。她慌忙用双手按住小腹,却将一对乳房暴露在我面前。比起英如梅来,蔡小妹的那一对乳房要说是乳房确实有点勉强。我以为她怕我笑的就是这个。我说:“这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脱我也知道。”我还体贴地将她抱过来,表示我确实没有丝毫要取笑她的意思。但是我感觉她的手还是那么紧张地按在小腹的位置。我想把她的手拿开。我说:“让我来。”她挣扎了两下,但终于还是放开了手。这样,我的手便按在了她的小腹上。几乎与此同时,我就笑了起来。蔡小妹听我这样一笑,便狠狠地在我的手上拧了一把。我猝不及防,哎哟一声,将那只手缩了回来。“说好不准笑的。”她生气地说。我想我是不该笑。如果之前我没有见过英如梅的话,它的确没有值得我发笑的地方。但我见过了英如梅,再见蔡小妹,就不得不笑了。我笑是因为它们完全不同。那时候,我真的还没有听说过什么白虎不白虎。我以为女人都是一样的。我的笑仅仅是出于一种意外和惊奇。我可以向那个谁保证,我是完全善意的。但我怎样向蔡小妹解释呢?我毕竟是笑了。于是,我对她说:“我笑是因为我喜欢。”蔡小妹看着我,将信将疑。“听别人说,这个要克夫的,你不怕?”她迟疑着问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说:“这是迷信。”
我是不信迷信的人。但后来听这样的说法听得多了,也有点心神不宁起来。所以,我问扬师傅:“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遇上了就会倒大霉?”扬师傅抽着烟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说:“这个东西,我看不见得。就说我吧,遇也遇上过了,还不是屁事没得?现在凡事都要讲个科学嘛。”他接着又哈哈大笑了几声,说:“我就不信那个邪!”
蔡小妹是个体裁缝,从早到晚都坐在缝纫机前。至少她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我早上出门时看见她坐在缝纫机前,晚上回到家,看见她还是坐在缝纫机前。有时候,我会以责备的口吻对她说:“蔡小妹,你不要命了吗?”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衣服,让她整天都坐在缝纫机前打个不停。有一次,我发现她打的根本就是一块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布。我问她:“这是什么?”好像被看穿了什么秘密似的,蔡小妹涨红了脸,又惊慌又尴尬。她甚至想把那块布藏起来。略微镇静下来之后,她告诉我,她是在练习一种缝纫的针线。我嘲笑她说:“你打了几年缝纫机了?还需要这种初级的练习吗?”她闷闷不乐。然后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我想给你打一个座垫。”后来那块密密麻麻布满针脚的四不像的布真的成了我那把旧藤椅上的座垫。
她对天黑感到恐惧。吃过晚饭,我一般要坐在灯下看一看当天的报纸。有时候是阅读刚收到的新的一期《无线电》杂志。收音机里播放着熟悉的器乐曲。这时候,蔡小妹就一直猫在厨房里。两个人简简单单的碗筷她却摸摸梭梭的要洗刷半天。我觉得她是故意的。我偶然闯进过厨房,看见她手里拿着一只碗站在灶台边发楞。看见这样的情景,我没有出声,怕吓着了她。其实我已经猜出来,她是磨蹭着不想上床,拖延时间。
“你不想生个儿子吗?”有次我问她。
那时候我们结婚都半年多了,但她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我以生儿子的名义,天天晚上要求她来一次,乃至两次。我说:“早栽秧早撘谷。”我还说:“要广种薄收。”我乐此不疲,但她却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她说:“我们不要再弄了,我是生不出儿子了。”
她好像还嫌一天到晚打衣服不够她忙似的,又养起了鸡鸭。房前屋后,充满了鸡屎味,鸭屎味。空气中经常飘忽着肮脏的羽毛。她故意把自己搞得很累,让我即使晚上和她睡在一起之后,想做什么也于心不忍。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为自己旺盛的性欲感到羞耻。既然生子无望,还瞎搞什么呢?当性欲失去了传宗接代的依据,勃起的生殖器就显得非常的可笑又可怜。我变得茶饭不思,经常性的夜不能昧,忍受着那种可笑的煎熬。这种日子让我慢慢地滋生起了一种悲观情绪,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狗,一只鸡。
张小惠是一个风骚的女人,镇上的人一般都喊她张大妹,可能是因为她的嘴巴大,胸脯也大吧。只有她的眼睛不是很大,但却很会勾人。她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我没跟她说过话。到镇上来一年多了,就去供销社买过一两回东西,因为平常买东西都是蔡小妹的事情。我知道她的名字,我想她肯定也知道我是谁。我们几次在码头的趸船上相遇,这种单独一起的机会,本来可以很平常地打个招呼,随便交谈几句。但我们却刻意地避开了目光,假装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样反而显得很不正常,好像是一种暗示,我们之间可能要发生一点什么。
我和张小惠的第一次是在陈家的水磨房。事隔几十年了,那些细节都历历在目。是油菜花开的时候。她一个劲地对我说:“别慌嘛,别慌嘛。”我就说:“你不要晃得太凶了。”我不能说女人就是我的理想,我知道这样说是得不到赞同的。但如果说理想就是一种幸福感的话,那天的那个时候,张小惠就是我的理想。
“拐得,拐得。”这是那天张小惠从嘴里频繁发出的一种感叹词。她摇晃着水磨轮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拐得。”她最后大喊一声,便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拐得”并非完全无意义的一个感叹词。它也是镇上人常用的一个土语。它的含义比较模糊和宽泛,看用在什么情景与场合。也可以说它是“糟了”的意思,比如不小心掉了一只碗在地上,“拐得”,蔡小妹会这样说。衣服裁剪得不合适,穿在身上才发现错误,蔡小妹也会说:“拐得,拐得。”也可以说是“惊讶”,“拐得,下雪了。”也可以说是“焦虑”,“拐得,娃儿跑不见了。”镇上的妇女经常这样大呼小叫。蔡小妹对我说得最多的是:“拐得,今天的鸡又下了三只蛋。”表示她的欣喜。
但是,张小惠与众不同,她只在那个关键的时候才说。她的这个发自肺腑的“拐得”,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一天,所长老卢说,他要找我谈一下。开始我还以为是跟张小惠的事情暴露了,结果不是。所以,只要不是我跟张小惠的事情,心里就一块石头落了地,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老卢要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县上分下来一个“右派”名额,他想来想去,这名额给谁都不合适,所以来跟我商量,让我把这个右派当了算了。他还说:“这个右派不是随便哪个都可以当的。是不是个人戴上这顶帽子还不像呢。县上的刘运权,这个人你听说过吧?秀才,笔杆子,能说会道,县长作报告都是他给起的稿子,怎么样?这次第一个当了右派。北京的就更不用说了,章伯均,中央的部长,毛主席都看重的人,怎么样?当了。刘绍棠,神童,顶顶有名的大作家。了不起吧?当了。你想想,比较起来,我们小小的一个高谷镇,就你的文化最高,上过大学,见过世面,这顶帽子你要是不戴别人还有哪个敢戴?”他说的没错。举出的几个人也是我知道并敬重的。但我还是觉得当右派不是件什么好事。我说:“要是当了,有什么好处?”老卢想了想说:“好处也说不上。但也没什么坏处。我问过上面,就是多顶帽子而已。你原来干什么将来还照样干什么。我也保证邮政所不会降你的工资。再说,你是得过一个处分的人,再多个右派的虚名,也没啥关系。我倒是想过,实在不行,就不去麻烦别个了,自己把这个名额顶了算了。但你知道的,我一个大老粗,唐诗背不来一首,道理说不出一个,顶个右派的帽子,那不是鸡脚神戴眼镜,假充圣人嘛?我脸皮薄,怕被人笑话。”经不住老卢的诚恳,我在几分犹豫中,还是答应了他。我说:“老卢,是不是没人戴这顶帽子你这个所长就很为难?如果是这样,我当了,算帮你老卢一个忙。如何?”老卢一下舒展了眉头,乐呵呵地说:“仗义。我就佩服你这种仗义的人。想不想打个牙祭?走,到吴二的馆子去,喝一盅。”
老卢在1957年欠了我一份人情。不仅我这样觉得,老卢自己也一直是认帐的。尤其在“文革”那些年,老卢看见我就躲。他自己都说,看见我落难的那个样子,最抬不起头来的是他自己。这是另外的故事,这里就不说了。
我当了右派,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妻子蔡小妹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她摔了碗,还不解气,又摔了一只洋瓷盆子。她哭着冲到院坝里去,我又听见她踢飞了一只公鸡。她蹲在院坝里的一棵石榴树下哭。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她不应该哭。因为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她这样呼天抢地,完全是小题大做,庸人自扰。但站在她的角度,我又觉得她应该哭。因为我是她丈夫,丈夫当了右派,而且还当得这么莫名其妙。她怨我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她商量一下。“你还当我是你的婆娘吗?”面对她的责问,我无言以对。但我又必须做出解释,才能止住她的哭声。我说:“老卢都说了,右派是个虚名,当了也不影响什么的。”听我这样说,她呼的一下站起来,石榴树也为之震撼。她说:“卢胖子的话都听得,老鼠药也吃得了。”她这样说老卢,我有几分不悦。我说:“你别忘了老卢还是我们的媒人,他会害我吗?”她依然哭着,说:“他当媒人就是害人。”我听她这话有点不对,话中有话,像是有所指。“你什么意思呢?”我问她,“当媒人害人?害谁了?”蔡小妹突然用一种陌生的表情看着我,接着冷笑一声:“害我了。敢说不是?”她这句话说出来,一点没带哭腔。她一下就平静下来。这样的平静,让人惊奇。我倒希望她一直哭到晚上。我希望她不理我,而让我去哄她,抚摸和亲吻她。那个时候,她会边哭边说:“我恨死你这个短命鬼了。”为什么是“短命鬼”呢?那是她无意中一次叫出来的。那一次她没有厌恶我摆弄她的身体。她还主动抓住我的手,把手心都抓出了汗。我让她抓着,心里想,简直是破天荒啊。接着,她就喊出了那一句:“你这个短命鬼啊。”虽说语音急促而含混,但我却被这三个字实实在在地感动了一个晚上。我想像她那天还会是那样,一直哭个不停,让我有一个做“短命鬼”的机会。但那天,蔡小妹平静地坐在灶门前,已经开始忙着做晚饭了。她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生火,添柴,烧水,搭米,切菜。咚咚咚,咚咚咚。没有想像中火钳烫了手,菜刀切破指头的那种慌乱。而是跟平常一样,有条不紊,从容不迫。那种表现,简直就像个圣徒一样。
有一天,我又去找张小惠。是晚饭后,天擦黑,有点风。在路上我已想好了,进门就把她按倒在床上。两天没碰她了,我有点迫不及待。我想她也是一样的吧。却没想到,会在那里遇见她的男人。早就知道,张小惠有个在外面劳教的男人,叫宋儒鸿。据说是因为犯了盗窃罪,三年前就被送去忠县的一个劳改农场。看样子是刑满释放出来了。他正坐在一根矮板凳上捧着一大碗面条狼吞虎咽。墙角的一个被盖卷捆绑得四四方方的,还没来得及打开,估计也是刚回来没多久。他从碗口上抬起头来,我们四目相对,搞得我进退两难。一句话,搞过人家的婆娘,自己是心虚的,怎么样都做不到理直气壮,气定神闲。但张小惠这个女人似乎没我想得这么多。她还跟平常一样,嘻嘻哈哈的,把我招呼进屋。她男人的表现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捧着碗从矮板凳上站起来,对我一个劲的点头哈腰。我听见张小惠对她男人说:“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马哥,高谷镇顶顶有名的大右派。”那男人越发的谦卑,还硬挤出满脸的笑容,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咕咙咕咙”的声音。说实在的,这情景让我浑身都不自在。我是一个讲礼的人,见别人对我这么客气,自然也不敢怠慢。张小惠的男人对我点头哈腰,我也只好对他毕恭毕敬。然后,张小惠就把我按到桌边坐下,硬要我和他男人一起喝杯酒。她先从床下的一只瓦坛子里抓了几把花生出来,堆在桌子上,让我们先剥着花生吃,自己又进厨房去炒了一碗鸡蛋出来。“你们两兄弟好好喝几盅。”她拿起酒瓶子分别往我们的酒盅里添满了酒。她男人双手捧起酒盅,朝我举了举,我也端起酒盅,各人喝下一大口。这样的场合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心里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幸好有酒。酒能壮人胆,也能解人愁。几盅酒喝下去,我就晕晕糊糊的了,话也多起来,几乎就忘了和我喝酒的人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和他喝酒?“宋儒鸿,你的名字很有来头。”记得我那天还这样夸奖了他。
我那时虽然已经是个右派,但也不想自己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单是他的那个长相我就很不喜欢。贼眉鼠眼的不说,两撮鼻毛像两支毛笔一样从鼻孔里伸出来,是最让我厌恶的。但这个宋儒鸿,成天无所事事,加上又是劳改释放这个身份,镇上少有人理他,于是三天两头跑来找我,我见到他比见到他老婆张小惠的时候还要多。我不喜欢,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我去码头接船,他也跟我一样准时地出现在趸船上。从班船上接邮包的时候,他总要伸出手来帮我搭一把力。“哥,你小心点。”他这样说。我扛了邮包去邮政所,他也跟在我屁股后头。我骑车下乡,他还想跟着走。我有点不耐烦。我说:“好了好了,你去忙你的,别老是跟着我。”他笑嘻嘻地搓着两只手,很不情愿的样子。我也知道,他没什么可忙的。但我就是不想他成天苍蝇一样的跟着我。我送信回来了,刚进镇口,就看见他蹲在那棵老白果树下。“哥,去吴二那里喝一盅。”他拦住我说。我疲惫万分,脸色难看。再说天也不早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想喝酒。”他诡秘地一笑,说:“上午我到窦家坝的斑竹林转了转,猜我搞到啥子好东西了?”我说:“猜不到。”他嘿嘿笑着说:“两只竹鸡。中午的时候我就放到吴二馆子上去了。我跟他说,等我哥晚上回来,当下酒菜。”他一口一个哥地叫着,还有他说的竹鸡,我怎么好拒绝?如果哪天他在镇上碰不到我,还会直接找到我家里来。我妻子都习惯了。蔡小妹也真是个好人,她是不是讨厌张小惠的这个男人我看不出来。但我不喜欢这个人,她是肯定看出来了的。尽管这样,她也并不会跟人家做脸做色。她表现得跟任何人进了门一样的热情、周到。端凳子给他坐,倒开水给他喝,还随口聊几句没什么实际内容的客套话。宋儒鸿也是嘴甜得很,一口一个嫂子,叫得就跟真的一样。他每次也不是空着手来的,手里总要提点什么,一只竹鸡,一串螃蟹,或是一碗斑鸠蛋。理由很充分,拿这些野味来做下酒菜。都窜进家门来了,我哪还有躲闪的余地?更让我不快是,张小惠也因此有了常往我家走的借口。每次都是,我陪她男人在桌上喝酒,她就陪我妻子蔡小妹在离桌子不远的床跟前说话。有时候两人说着说着,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怪怪的笑声。张小惠笑的时候,还总拿眼睛往我这边瞟。我觉得她们有可能是在说我什么。我不好问蔡小妹。但我后来问过张小惠。我问她:“你们在说我什么?”张小惠说:“哪个在说你哟?”我又问:“那你们笑什么笑?”她说:“才怪呢,笑都笑不得了嗦?你那么不放心,回家问你婆娘去,看我们是不是在说你什么,在笑你什么?”
我没问蔡小妹。我已不在乎她们说我什么,笑我什么了。不久,也就是1958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自带被盖和洗漱用具去县里的学习班报到。
这是非去不可的了。看通知上的那个语气就知道,这个学习班是带有强制性质的。
蔡小妹在为我收拾行装的时候,神情中也流露出一种担忧。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不得去找她的。”为了证明我此言不虚,我还说:“你看这么久了,连一封信都没写过。”但我实际上是误解她了。她根本不是担忧我到了县城会去找原先那个害我来到小镇的女人。她是在为我的政治生命担忧。1957年之后,再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渐渐地明白过来,右派已经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栓在一根藤上的阶级异己分子。这等于是被打入了另册,以后的日子必然没什么好果子吃。这一点,在我还比较糊涂的时候,蔡小妹就凭她的直觉预感到了。那天,她又替我将冬天的衣服都收拾进了行李。我是到了县城住下之后,打开那口箱子才发现的。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心里清楚得很,进了这个学习班就不是那么容易回得来了。她真是有先见之明。
我们后来将这个学习班称为“右派集中营”,又叫“和尚班”。全县的右派都被集中到这里来了。而且,一开始我就发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全县三十二个右派,居然没有一个是女的。我毫不隐瞒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期待,那就是,在这个学习班里至少能够碰到一两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女人。等到宣布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的时候,我就彻底地失望了。如果说之前还没把当右派看成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但从这时候开始,我便明确地意识到,不能再对右派的前景抱有丝毫的幻想了。
一个女人曾经对我说,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你只爱你自己。这个女人是谁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这些年,我经常梦见自己到了月球。或者说,置身于一个类似月球那样的环境。身体变轻,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但所到之处皆荒芜。火山灰,这三个字往往要在我醒来之后纠缠在我的思维中长达数十分钟。我的妻子已经死了有些年了。我就是在她死的那一年,开始梦见月球的。我妻子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我要死在你前面你就惨了。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而言中。
蔡小妹,你说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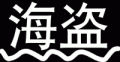 ┩目录┡
何小竹,男,1963年生。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6个动词,或苹果》,小说集《女巫制造者》及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等。现居成都,为居家写作的自由职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