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我的没有实现(续集)
◎ 赵猪
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那几年我到底在干什么了。最起码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是肯定都记不起来了的。对了,那几年我还在写小说,天天如果我是坐在教室里上课的话,就会闷着头,拿着笔写很多东西,也不听课。或者我还会到校门口一个朋友的店里去玩,看小说,看武打小说,言情小说,看漫画书,把以前看过很多遍的书再多看上一遍又一遍,就当自己从来都没看过一样。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朋友陪我一起玩,大多数都是男的,除了做乐队的朋友外,我也有很多根本都不听音乐的市井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讨论赚钱,讨论女孩子。说一些很下流的话,也只是说一说而已。然后他们一个个就都不见了,因为时间很晚了,他们最后都还是有女朋友的,总是要回家去陪的。
我记不起来,这样的时间过了多久。
一直到有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家里无聊地看着达明一派演唱会的时候,阿勇和他的老婆来敲我的门了。这离他们去江浙还不到两个月吧?我记不太清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又回来了,然后,阿勇对我说了一句话,赵猪,来跟我们一起做乐队吧,你吼叫的时候,挺过瘾的。那个晚上的灯光可能是太昏暗了一点,不然,阿勇应该会发现我的脸红了,是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的。我其实并不会唱歌,但是如果可以把我的嗓子变成一个人声乐器,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的话,我想,也是件很酷的事情吧。
我们开始排练了,正式地象一个摇滚乐队那样排练了。排练室换了,在阿勇他们上班的歌厅里,器材很全,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舞台,虽然大多数时候,台下坐着的还是张华的老婆,阿勇的老婆这些人,但是我觉得很兴奋。
赖四平不想再玩乐队了,因为在观念上有分歧,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缘故。现在张华做了吉他手,要要去弹贝司了,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真的做了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声乐器。其实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对乐队什么的完全一无所知。
我不识谱,不会任何一种乐器,鼓学了一段时间,还找不着拍子。我想那段时间,阿勇他们为了迁就我,一定伤透了脑筋。所以我拼命地写歌词,希望写出可以让他们满意的,拿出去又能叫得响的歌词。但是我没想到,这方面,我也废了。
我那时期过剩的社会责任感和青春的热血使得我走上了我完全不熟悉的一条道路。我向盘古致敬,向舌头致敬,向一切我知道的当时的朋克乐团致敬。但是我从没发现过,我根本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胆小怕事得很,而且十分满足于既得利益。
我唯一反抗的不过是我的家庭和教育环境而已。然后我写了貌似强硬,但是骨子里头软弱的《歌唱祖国》。我以为那很了不起,其实更应该被“歌唱”的是我们自己。我写乱伦,其实前言不搭后语的歌词里没有任何一个意向是能够拼凑在一起。最好的其实不过是那首软绵绵的情歌《夏洛特的网》。我天生软弱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抒发,我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恋爱经验的可怜虫而已。
另外说一句,这首歌是献给我当时的女朋友的,我在聊天室里认识了她,莫名其妙地就把她当成了我的女朋友。我很感谢她,我终于不再是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了。要要很为我高兴,他说赵猪应该找个女朋友了,不然,就真的变态了。因为我当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有事没事地掏他们的小鸟,摸他们的屁股,然后就惹得他们跟我打在一起。
在这里又要说到邵阳,说到拆乐队,说到丁孜了。
在2000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到了邵阳排练,三支乐队在一起排练。用的乐队班底其实是同样的几个人,阿勇打鼓,张华弹吉他,要要时而弹弹贝司,时而做点别的。
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当时他们从江苏直接去了邵阳,然后阿勇跑回了郴州,叫上了我,我才正式地成为了手乐队的一员。
拆乐队当时在阿勇和张华的帮助下,完成了从一支GRUNGE乐队到低调华丽乐队的转变,张华改弹吉他还没多长时间,但是那些连他自己也记不住的古怪惨情旋律却似乎是天生就该与王志超尖利嗓音配合在一起的。李勇离开了长沙的疫乐队以后,和阿勇他们组成了落乐队。从这个与英文字母“LOW”几乎同音的字母大家应该都能了解了吧?他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还是没办法融入到乐队中去。
当时我喜欢EN,喜欢实验音乐,但是阿勇他们更喜欢重一点的,暴躁一点的东西。在配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说我们做的是硬核,但是张华的一把吉他始终还是单薄了一些,而我根本不能很完整控制的嗓音,也在大多数时候都跑出了圈外。我知道,我其实根本都不适合做乐队的。
丁孜是第一个把JOY DIVISION当作THE
CURE卖给我的人,他还同时卖给我了一盘EN的带子,卖得很贵,当时他做演出赔了不少钱。我能理解他,但是我不原谅他,因为我当时也没钱。但是在一次湘潭的演出上,在那次我生日的酒会上,他跟我碰了几杯酒,聊了聊大话西游,我们又成了好朋友。我是个很容易嫉恨人,但也很容易就喜欢上一个人的没原则的家伙。
我们酗酒酗得更凶了。在邵阳的时候,我们住在邓卫松的房子里,没事就喝邵阳大曲,喝多了就听很重的音乐,比如内阁,比如KMDFM。甚至是化学兄弟。然后在那个夏天里,阿勇的裸体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恶心的东西。
除了喝酒,排练,我们就上网去聊天,在当时很著名的高地聊天室里到处撩人吵架。我打字的速度就从那时候练了出来。我们四五个人一起进去骂人,变着法儿惹人,骂人,到处吵架。我们做不了现实中的暴民,就只能这么发泄我们的欲望。
夏天过完了,我们回到了郴州,生活好象又一下子恢复了平常状态,他们继续上班,我继续上学。除了继续上网,吵架,骂人,谈恋爱。唯一能证明我们的,就是那张录了十首不成熟歌曲的小样了。
郴州的秋天一般都很热,潮湿的空气里,我们的血却渐渐凉了下来,我想,如果没有一点新的刺激,我们就会慢慢枯萎了,起码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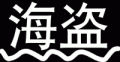 ┩目录┡
赵猪,前湖南手乐队主唱,现在的文字工作者。在北京,但是想回老家。最近的爱好是戏曲和山歌。岭北山区人,却长了一张北方人的屠夫脸,很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