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 大拿
96年我23岁。在我的离婚计划失败后,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去齐齐哈尔搞乐队。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应该把“乐队”二字用“女人”替代更符合实际。但是,老天在上,我的初衷真的是去搞乐队。
以家里所有的存款为代价把老婆暂时打发回娘家后,我怀揣几百元巨款来到了齐齐哈尔。用尽了花言巧语哄我“出山”的哥们携乐队全体成员在齐市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酒馆热情地招待了我。席间,我搞清楚了乐队的阵型:吉他
33岁 齐市人 据说是齐市最牛比的吉他手(之一) 乐队的灵魂(那会时兴这种说法);鼓 26岁 齐市人;键盘 20岁 吉林四平人 ;贝司 19岁
讷河人;主唱
暂时空缺。原来哄我出山的哥们在乐队里并无位置。我们就音乐领域的问题广泛地交流了意见,基本达成了共识。吃到最后,当我看着桌上的一堆空盘子提议结束这顿午餐时,哥几个同时用瓦蓝瓦蓝的眼神凝视着我,其中一个说:还没买单呢。
乐队的排练场地在鼓手家。那是一间装修得极为精致的平房。惊人的是,房间内所有的家具,包括精美的木雕和不逊于五星级宾馆的卫生间,居然都出自鼓手一人之手。这让我在肃然起敬的同时又有点毛骨悚然——这哥们活得也忒在意了。后来贝司告诉我,这本来是鼓手打算用来做新房的,结果在婚期临近时,却和未婚妻吹了,原因不得而知。
第一次试音时我就傻眼了。他们给我的话筒不仅没有混响延时等效果,就连音量也很有限。而且还是和吉他共用一支音箱。我只能扯着喉咙声嘶力竭地完成了老吴帮我选的《怕你为自己流泪》……
接下来的记忆就有些混乱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饿。当时键盘和贝司租住在齐师院对面巷子里的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里。房东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老太太。她自己住一间,我、键盘、贝司和另外二个音乐系的学生住剩下的一间。伙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们预订饭菜,老太太给我们做,我们付钱。付款期限是一周。我想是我刚来时那次饭局买单时的举重若轻给他俩造成了错觉,导致他俩很快就帮我把我带来的几百元巨款挥霍一空。接着我们的食谱就变为:早
馄饨 午 馄饨 晚 馄饨 。然后是:早 无 午 馄饨 晚 馄饨
再然后是:每日一碗馄饨……最高记录是:我们三个人三天总共吃了二碗馄饨。这还全靠我偶尔回大庆市跟我的前乐队干几场婚礼庆典什么的卖唱弄点钱来维持。要命的是,我大庆乐队的键盘是个女的,而且貌美如花,柔情似水。更要命的是,她丈夫是我们那个乐队的鼓手(这又是一个令人断肠的故事,在我另一篇文章里)。这么说你明白了吧?我真怕我哪天把持不住呀。但没办法,吉他(灵魂)坚决不允许我们出去参加任何演出,也不打算弄自己的作品,每天就是排练,再排练。练的都是别人的东西。这也是我后来退出乐队的主要原因。他的想法是:十年磨一剑(他磨的都是别人的剑呀),有朝一日去北京等大城市走穴。可他自己却每晚在舞厅伴奏,弄个百八十元的,还自己花。
当我从大庆弄了点银子回到齐市蜘蛛侠般出现在他俩面前时,他俩蓬头垢面柔弱无骨望眼欲穿的样子,总能让我想起《甲方乙方》中那位被送到陕北农村住了一个月的大款。
这些只能说明我们艰苦,却不能说明我们痛苦。事实上我们那时一直是穷并快乐着。因为有理想和信念支撑着我们。每天早上我们从驻地出发,穿过一条冬天里已经干涸的小河,经霁虹桥,过解放门,再穿过一个露天市场到鼓手家排练。完事再回去。往返大约六公里的路程。那时可真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性生活基本靠手。排练的内容主要是黑豹、指南针、逼养子(黄家驹他们)、赵传等。都是别人的东西。我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还是用那支破话筒。直到有一天排《眼光里》。你知道,那首歌的高音区很密集。我对吉他说,你就是把窦唯找来,用这支破话筒他也唱不出来。最后他妥协了,把他以前用过的吉他效果器给我弄来几块接到话筒上。那是一种很古老的效果器。一块合唱,一块延时,好象还有一块失真。虽然不很理想,但聊胜于无。出来后的效果倒颇有点神似后来的刀郎。
接下来就该谈到女人了。
键盘的女友名唤李阳,是一位有着马拉多纳式粗壮身材的姑娘。肤色白皙,性格活泼。之前曾是键盘和贝司在音乐系的同学。后来退学在一家餐馆打工。凭心而论,这姑娘不错。在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她还接济过我们几顿。
一天李阳带来了一位姑娘,说是叫张丽娜,刚刚从大连回来。李阳打算在我们这里给她搞一场接风宴。在付清上星期拖欠的伙食费后,房东老太太给我们弄了一桌酒菜。当然,这一切开销均由李阳支付。虽然饿了好几顿了,但我的注意力还是没放在食物上。因为这位丽娜姑娘确实不错。肩宽、腰短、胸高、臀圆,长得很丰满,很立体,很欧美。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品位和普通的装卸工人没什么两样。与她嚣张的身材相反,丽娜为人比较随和,也很乖。经过短暂的眼神交流后,不顾如饥似渴的贝司,毅然坐在了我的身边。于是我就晕晕忽忽地喝了很多酒。我俩的手在酒桌下面过招,由试试探探到纠缠不清难舍难分。后来甚至还当众接了吻。李阳说去我家吧。李阳家在富拉尔基区。她父母离异。母亲这几天又没在家。于是大家决定去李阳家涮夜。
你瞧,这么快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我们马上就要不顾一切的互相摸了。
李阳家只有一张双人床,只好横着躺挤一挤了。我们睡觉的位置由床尾到床头依次是:贝司、键盘、李阳、丽娜、我。丽娜用在她妈肚子里时的姿势面向李阳侧卧着,异常肥硕的屁股挑衅似地翘向我,我则用同样的姿势卧在她身后。躺下后不久,键盘和李阳就单刀直奔了主题,把个小床弄得风声水起动荡不安。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突然,我欧元般坚挺的生命之根被一把握住了。我也没含糊,以牙还牙地把手伸向了她的帝王将相(不是曾经有个女人拍着自己的阴户说帝王将相皆出于此吗?),而那里,早已是一片汪洋……接下来我当然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了,事实上我也在做了。
然而,就在此时,就在我刚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我的精锐部队打入到敌人内部时,整个局面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李阳她妈回来了。我对我家的马桶发誓,我的精锐部队刚刚打入到敌人的内部,还他妈一次迂回都没来得及做呢。终归是有在学校时踢前锋的底子,哥们的反应就是快,我在她妈开灯的同时扯过了一条被子盖在了我俩的腰间。之后我就闭着眼睛一直没有睁开,也没有说话,丽娜也一直没有说话,和我一样作熟睡状。我们的睡姿看上去应该像个被去掉一半的书名号。幸好是盖了被子的书名号。如果你揭开被子就会发现,这半截书名号内部还有一个减号连接着。最气人的是,几秒钟前还在莺声牛喘的李阳两口子居然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和她妈聊起了家常。睡着前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俩傻逼刚才肯定是盖着被做的。
然后我就睡着了。我没有撤回我的精锐部队,我俩就这样联体婴儿般地睡了。
排练,再排练。
赊帐,吃饭。再赊帐,再吃饭。
当时我们除了排练就是听歌,听丑丑(指南针最初不是罗琪),听秋野,听二十一,听窦唯张楚何勇们的香港红勘演唱会,听超载,听双子星,听单行道,听盘古,听麦克尔杰克逊,听好多不知道名字的外国乐队。
当时最喜欢的是双子星乐队中郭亮词曲并主唱的一首歌,歌名忘了,只断断续续的记住了旋律和几句歌词,好象是:……两颗心 正在摇摆,从天上
飘过来,我和你飞向彩虹,一路上 忘了伤害……是你让我这样寂寞 还是我拥有你(变成你) 是你让我这样升起 坠入 这无尽的游戏……
奇怪的是,这首歌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去了好多音像店,也访问了好多网站,都没能找到。而且,和其他搞乐队的哥们提起时,也很少有人知道周迪和郭亮曾经搞过一个叫双子星的乐队。这让我很是惆怅。
还喜欢高旗的“九片菱角的回忆”,还喜欢窦唯张楚何勇们的香港红勘演唱会,等等等等……我认为他们那才叫唱歌呢。
现在想想,我对歌的喜欢基本上到许巍、朴树、刀郎他们这为止了。周杰伦以后的歌基本没法听了。尤其是周杰伦,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红。我不由为下一代人的鉴赏能力而担忧。和那些人比起来,我认为周杰伦甚至都称不上歌手,充其量他也就是个行吟诗人,而且还是口水型的。
还是说说正经事吧。贝司19
岁了,还没沾过女人。这让我们很着急。每当我见到他用火辣辣能麻死个人的眼神看丽娜时,我就会感到很过意不去。这哥们实在是被素得太狠了。于是我就经常鼓动李阳丽娜给他发个姑娘。
终于有一天她们带来了一位。名字记不清了,好象叫什么霞。是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姑娘。很文静的样子。属于偷着胖的那种(这是贝司后来告诉我的)。也是他们以前音乐系的同学。后来也退学了。据说现在做小姐。可我怎么看她也不像。
我们住的房间有三个上下铺。贝司住下铺,键盘在他上铺,我在他对面的上铺。那时另外两个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了。也就是说,这个房间被我们这三对狗男女占领了。那天丽娜来月经了。所以我们剑拔弩张的听了半宿,却无所作为。天知道,对着一个面积比脸盆还大的丰臀,这有多难。键盘他们轻车熟路,很快就大公告成心满意足地打起了呼噜。贝司他们倒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听那意思似乎是贝司有点疼,先是进不去,进去后又不敢动,后来在什么霞的调教下终于上道了,却又射不出来。听了什么霞美妙绝伦的叫床声后我相信她是小姐了。折腾了半天之后,贝司忽发奇想,非缠着什么霞教他玩女上位。可能是考虑到还有另外四位在场,什么霞不同意。但最后终于拗不过他的苦苦哀求,还是做了。我居高临下扭过头去,看到月光下一具灰白圆润的肉体,在做着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动作,再加上摄魂夺魄的配音,真真是美不胜收,叹为观止。那是我唯一看过去的一眼。后来我就抱着丽娜巨大的乳房睡着了。
我们乐队的乐器都是不错的。吉他用的是八千多的雅马哈,亮蓝色的琴身,浅木色的琴颈,看着就招人喜欢,效果器也是五千多的合成块。贝司光效果器就六千多。键盘是一万五千多的罗兰50。鼓加上后买的牛铃已经超过二万,而且还打算再添置康佳手拍鼓。这些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配置了。想起键盘和贝司两个刚满20
的大孩子背井离乡,每天上顿不接下顿地饿着肚子,背着高档乐器步行往返六公里去排练我就感动。遗憾的是,吉他固执地不肯搞乐队自己的作品。还是排练人家的东西。这让我很失望。最后我终于决定退出乐队。临行前丽娜设宴送我,大家都很动感情,执手相对泪眼,差点没无语凝噎。哎,这帮哥们,这个有情有义的女子!
很遗憾,我最终也没能和丽娜做一把背入式。我曾无数次的设想,如果她跪趴在床上,撅起屁股,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呀。怎奈我们那时排练很紧张,她也忙,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场地又成了问题。这些都解决了,她偏又来月经了。造物弄人啊。我不禁想起了海涅的悲歌:
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朵紫罗兰熠熠生辉
这轻狂的姑娘!
我竟未染指
妈的!!
我好不后悔!!!
不管怎样我还是怀念那段日子。怀念我们的执着,怀念我们的落魄,怀念我们的乐队,怀念那有情有义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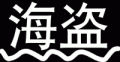 ┩目录┡ 大拿,老帅哥,73年生于黑龙江。此后长于黑龙江,极有可能在未来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老死于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