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 狗熊的红领巾
约好要和一个编辑谈稿子,可是当我打开QQ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不属于我了。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曾输了五遍密码(由于以前有过连续输错四次的纪录),最后一遍是一字一顿着输的,得到提示后,我想,完了。我的QQ里头大概有四十个人,五个群,大部分时候是用来扯淡,偶尔说说正事,比如今天。眼看着已经到了约定时间,人家可能早就上线了,报着不甘心的态度我用另一个号码登录,看见名单里的我已被更名为002,我想,真完了。
看来只能失约了。有没有可能让他把号还给我呢?哪怕是一会儿,过后我可以送给他,他会相信么?我试着跟他说话,语气不是很强硬,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已气急败坏,况且那样没有任何作用。我甚至用了“你好”,我问他能不能把号还我,他没回应,好吧,那条件降低一点,能不能先借我一下?我有急事。一小会就还你。还是没回应。我想他如果在线的话,可能在笑。他会把身体靠在椅子上,两腿伸展,总体呈一个最放松也是最适合笑的姿势,笑够了,他点上根烟,猛嘬一口说,靠。当我是傻比吗?好吧,那能不能帮我告诉某某一声呢?就是大鼻子头像的那个,很醒目的,就说我的QQ丢了,再约。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一个贼偷了别人的QQ,又主动通知里面的人,说本QQ已经被盗,请勿再骚扰。答案是否定的,从情感上讲也不大行的通。因此他继续沉默。
我感觉很差,愤怒只是一部分,还有无奈、悲伤,如果能找到那个贼,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理由已经够充分了。我承认,QQ对我一直是件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不只一次地对它表现出厌恶和轻蔑,我不只一次地清理它,丢弃它,甚至想要毁掉它,可如今它真的丢了,尽管它依然不重要,但那毕竟是一件和我有关并且一起存在了多年的东西,就像我一个素未谋面乃至避而远之的农民亲戚,一天他死了,听到消息,我仍然会难过。此时此刻,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无奈,那种弱势群体特有的、无法反驳的、失语的无奈。
抽了根烟,我默默想了一会我的QQ,以示哀思。它的生平如下:
编号:17849439,生于2000年9月,北京。姓名:红领巾,曾用名:地球女孩、作好事不留名。面貌:普通。职业:聊天。
2001年2月,调至河北,更名“作好事不留名”。继续从事聊天活动,以成人为主。
2002年6月,更名“红领巾”,开始涉及文学、电影、性。
2003年10月——2004年10月达到G点,工作繁忙,仅群就达16个。
2004年底,首次遭封杀,退群、名单大清洗。
2005年6月,开始从事投稿、讨论、扯淡工作。
同年10月,第二次G点。
同年12月,第二次清理。
2006年始,深居简出。
2006年4月10日,猝。
除此之外,我还想起一则利用QQ从事诈骗活动的新闻,眼下里面的朋友,都是经过历次清洗筛选出来的,我以为,骗起来还是不难的。于是我开始动用手机,邮件,论坛,博客,MSN等一切能动用的东西通知他们,一是声明QQ丢了,二是发动大家骂他,然后删了他。一口气发了若干,很爽,但心情依然差,我对着电脑,不知道干吗。我觉得自己就像只丢了壳屋的寄居蟹,在网上横冲直撞,我远远地看见那只本来属于我的壳屋,尽管它已经长满青苔,破了旧了,但那里头仍有我的气味,我的习惯和记忆,现在它已经不属于我了,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它。妈地,这感觉差透了,就像让人给干了。后来我在MSN上碰见乌青,我说我QQ丢了,他说可以找回来呀。我恍然大悟。我打开腾迅主页,面对一堆表格终于还是没填,我想填它干吗呢?我已经通知朋友们删了,要回来也是个空壳子。
心情依然差,我决定出去走走。已经是春天了,一年一度的沙尘暴即将来临,路边的柳芽初现端倪,只差一场沙尘的洗礼。过马路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寄居蟹的事情,于是倍感脆弱,我想热闹的地方一定充满危险,还是走远点吧。我决定打车去海边,拦车的时候我在红、绿、黑三种颜色中选择了一下,最终决定选红。不知道我算不算个生性多疑的人,不顺心的时候就特迷信。我在离海不远处下车,想走一段,我看见远处的海,在一片雾气当中,没有界限,几只船恍惚移动着,形迹可疑。路过小市场我买了一个贝壳手链,十块钱,我知道上当了,但懒得矫情。
在海滩上走了一会儿,没什么意思,风太大,吹的人难受,就坐下来,还是没意思,风仍然大,仍然吹的慌。我想要是再过几个月就不会是这样,到时候满眼都是林立的大腿,根本顾不上风。
我是在卖当劳碰上韩录他们的,他们招呼我过去,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看见他们了,我没吱声,是想自己待一会儿。不过我最终还是过去了,坐在他们中间,有人帮我要了杯可乐。他们是来风吹的,六个人当中,一对夫妻、一对尚不明朗,另外两个毫不相干。不相干的女人叫刘虹,和我是大学同学,毕业分到银行,已经几年没见了。我跟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沉默,她则看着我,好像坚信我后面还会有话。同学重逢哪能这么简单。我沉默的时候她就一直盯着我,我忽然被这蠢女人搞得很烦,就抬起头来跟她对视,但是我只坚持了数秒就败了,确实不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个腼腆的人,平时说话都很少看对方的眼睛。刘虹笑了,她的声音有点粗,就像田震那种。她问我过小玉来我为什么不露面。我看了眼韩录说,有鬼缠身。她说是狐狸精吧?我说不是,是饿死鬼。说完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笑了,只有我一点没笑,刘虹说,小可你情绪不好呀。
我说没有。韩录说,还说没有,自从没见成过小玉你就一直这样。他说“见”的时候故意把音放平,形成另一个字眼。我不得不解释一下了,我说我的QQ丢了。没想到韩录紧接着说,靠!QQ丢了也至于这样,还是不是个男爷们。我无言以对,我说过我是个腼腆的人。还好枫丹帮我解围了,她说怎么不至于了,我也丢过一回,Q币衣服宠物什么的全没了,气得我哭了半天。李熊说可以找呀,他也丢过一次,当天就找回来了,网站上挂失的多的是,每天不知道得丢多少。借着这个话茬,我们聊起了网上的事儿,论坛、视频、博客、八卦新闻、小道消息、馒头、郭德纲、罗永浩、时政分析、黄色网站……后来又绕回到QQ,刘虹忽然说,千万别乱动别人的QQ啊,会遭报应的。说完她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她的一个同事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小伙子,聊了几个月,彼此都感觉挺不错,但是没有见过面,在这个问题上姑娘还是很谨慎的,毕竟是网友,被网友骗的事情比比皆是。于是又过了几个月,说话他们认识就快一年了,小伙子一如既往,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情绪。姑娘想或许可以见面了,之后呢,就是恋爱,结婚,生活,但一想到这,她又犹豫了,她觉得还是应该再试探一次。这次的方法是,找人帮她盗取了他的QQ号码,她想如果他对自己是真心的,那他一定急疯了,他一定会来找她,求她把QQ还给他,他会告诉她这对他有多重要,他是多么爱里面的那个姑娘,失去QQ就等于失去她,失去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盗号之后她就很兴奋,上线等着小伙子来找她,她认为这是肯定的,到时候她会感动地痛哭流涕,把号码还给他,然后见面,嫁给他。新婚之夜他把她搂在怀里,给她讲这个故事,他说我们的爱情把小偷都感动了。然而,小伙子没有来,她等了很久,每天二十四小时在线地等,她急了,她坚信小伙子是爱她的,那他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些呢?她真的有点着急了,终于把密码改了回去,然后等他来。仍然没有。她开始怕了,她忽然发现除了QQ他们对彼此一无所知,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他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干脆就是个来自于地球之外的生命,不受任何控制。她疯狂地在城市里寻找,但是诺大的城市,茫茫人海,谈何容易呢?他就这么和QQ一块消失了,几乎是永远。她带着这种绝望的情绪整整过了一年,她开导自己,既然他没有回来,说明他根本不爱她,她曾无数次地试着说服自己,但无数次都失败了。后来她带着这种矛盾嫁人了,嫁给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整天醉酒,谈生意,谈生意,醉酒。她很寂寞,但再寂寞,也不敢用QQ了。
这个傻逼。刘虹讲完之后,又冷静地总结。
是不是真的呀?顾骊问。
当然,你可以去行里问,都知道。刘虹说。
靠!能写个小说了,小可你就写写这个吧,韩录说,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千万别乱动别人的QQ,包括其他。
六点多的时候,沙尘暴正式开始了,天空中铺满黄土,上下都是地,没有天。状观极了。我忽然想到一个词,改天换地。好在他们是开车来的,七个人,两辆车,不挤。我们三个耍单帮的一路,车是刘虹开来的,奇达,我讨厌日本车。由于天气的缘故,车子开得很慢,几乎是在爬行,如果不是那些沙尘,我倒宁愿下车步行,我们都已经进化到直立行走了,干嘛要爬呢?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刘虹说,废话,要不是这鬼天气,能爬么!她说的也对。
按照路线,我们先送李熊,我们把他扔在距他家不远的路口,然后扬长而去,当然这个动词只是我们的愿望,实际上并没有效果,因为一直在爬。车上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刘虹开始挑逗我,是赤裸裸的挑逗。她说了很多下流的话,充分表现出一个三十多岁女人的无所畏惧,我也说了一些,也下流,彼此都很高兴。刘虹点上烟,车里空气就很不好,她打开车窗,马上有土飞进来,是吃烟还是吃土,这是个问题。最后她把窗子开了个小缝,本想把烟弄出去,又不让土进来,没想到由于风大,立刻形成了一种蛮不讲理的正压,于是我们既吃烟又吃土,刘虹说,靠!然后讲了一个毛片里的术语,哈哈哈一连串的笑,由于抽烟,她的声音听起来更哑了。
按照路线,应该是先到刘虹家,于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怎么办?是到她家我下去打出租,还是她把我送去再回来,还是我开着回去第二天再还她,三者里面,我觉得中间的最理想。这件事我估计她也会想到,这正经是司机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她始终没说。我也不说。我们就这么沉默了,看上去各自心怀笸测。烟抽完了窗子再度关闭,空气不再流通,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有限的空气,她呼出来,我吸进去,我呼出来,她也吸进去,我们用这种方式默默交流着各自的身体,想想真暧昧。但是事情又很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吸入彼此呼出的气体,那些二氧化碳对我们来说毫无作用。我们只是在争夺着有限的赖以生存的空气,这样的话就不是暧昧,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事实。
在刘虹家前面的一个路口,她忽然对我说,你觉得那女的傻不傻?我没听明白,问,哪个?她说,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我想了想,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啊,她傻不傻呢?这或许不该是个傻不傻的问题,而应该是值不值得同情的问题。但如果一定要用傻不傻来衡量,那我只能说她是聪明过头了或者还没傻到位。刘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她伸出右手盖在我的左手上,我下意识地一缩。她清了清嗓子,说,那个女人就是我,我们都是被QQ刺激过的人。我没表现出惊讶,因为我还没想清楚。之后,我给她讲了早上看的一个片子,那是个韩国毛片的花絮,带剧情,男女主角穿着古代的服装,在一个柴房里,大概是要通奸,但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女的扑上去脱男人的裤子,两人发生撕扯。让我意外的是,这段戏居然拍了十几次,导演一次次地喊停,两个演员都很敬业,不厌其烦。天气很冷,女演员始终光着身子,看得出她一直在发抖,后来在作爱阶段,他们抱着相互取暖,空隙中,男演员还为女演员搓身体。看到这,差点就哭了。我居然让一部毛片给感动了。我说。空了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快到我家的时候,刘虹忽然说:一部感人至深的毛片,不是好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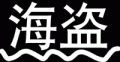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狗熊的红领巾,男的,胖子,不会游泳,住海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