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一条黑色的狗吗
◎ 吉木狼格
我家从乡下搬进县城前,有一条狗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神秘”这个词的含义。当老师在课堂上说出这个词,我只是觉得它很新鲜。而那条狗,它的神出鬼没、它的难以接近、它站在远处与我对视的姿态,总要触动我身体中的某一根神经,不由地我就兴奋起来。
它是一条黑色的狗,非常黑,比最黑的狗还要黑一点。
我养的小飞和何强养的二崽,以及它们的母亲跛子,经常集体跑出小巷,半天不回来。开始我以为它们出去觅食,并未在意。一天下午,在我家背后的悬崖边,我看见河谷对面与这边平行的山埂上,站着一排狗,其中就有小飞、跛子和二崽,那条长着花斑的狗也在。它们的中间是一条黑色的狗,非常黑,比在场的黑狗都黑。
我大声喊小飞和跛子的名字,我知道即使不用那么大声,它们也能听见,可是它们站成一排,一动也不动,仿佛在向我示威。
我觉得不对劲,它们怎么会不听我的话呢?要在平时,早就跑过来了。我猜这跟站在中间的那条醒目的黑狗有关,它究竟有什么能耐让我养的狗胆敢无视我的召唤?我对小飞和跛子生气的同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开始留意河谷的对面。常常是,先只有黑狗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就站满了一排,这些狗到来之前,我仔细地观察那条黑狗,它真是黑啊!
我决定靠近它,搞清楚它究竟是何方神圣。当它们又站成一排,我冲下河谷,顺着山坡往上爬。为了不让它看见,我没走小路,因为小路暴露在收割后的玉米地中间。我隐蔽在草丛中,像某种动物正在捕猎,我小心地一点一点接近猎物,快到山埂时,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准备作最后一击,也就是突然出现在它们面前。
我的突然出现,把站在山埂上的狗吓了一跳,但是,我也被吓了一跳,我在对面看见的狗都在,惟独没有那条黑狗。
我四处察看,四处寻找,小飞它们蹦蹦跳跳地跟着我,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和一条黑狗在一起。
也许它发现了我的举动,提前溜走了。
我又干了一次,这次我改变了方向,加快了速度。结果连它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两次失败,我总结出两点:一它太精明,二我不够隐蔽。我跟它较上了劲,不就是一条狗吗?我得想个办法,让它在我面前把脸丢尽。
我看见山埂下有一块凹处,平时它们就站在那上面。如果提前躲进凹处,等它们到了突然跳出来,看它还能往哪里跑?对,就是这样。
我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地来到凹处,蹲下后,我尽量往里靠,耐心等待着。不久上面有了动静,而且动静越来越大,那是它们用鼻子使劲嗅东西的声音,我估计该来的都来了。
这下你没说的了吧,我想。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上面的场景让我哑口无言,黑狗又不在。
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件事,做梦都在想。本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很正常,但我做的梦太不像话,人不人狗不狗的。它明明是一条狗,可是它坐在那里,以一副长者的模样,给围着它的狗讲熊家婆的故事。
第二天我直接来到对面的山埂上,其实我已经失去了信心,失去信心又要做某一件事,这就叫耍赖。从凹处到山埂,只需一瞬间的时间,现在我连一瞬间也不要了,我就站在这里,来不来由你。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几分自暴自弃,又有一种强撑的得意。
我终于看见它了,但不是在这边。它在对面,在我站着看这边的那个位置。同样的,起先只有它一个,接着它的身边就站满一排。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极其不好,仿佛我变成了狗,而它们是人。
还是各就各位吧,你们过来,我回去。
我问何强有没有看见那条狗,何强说没有,于是我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
“是狗王,”何强说,“它不喜欢人,只和狗在一起。”
我从没听说狗也有王,假如狗真有王的话,这条黑得不能再黑的狗,应该就是狗王。我在想除我之外,还有谁见过它?
前不久我们刚学了一篇课文,是一个记者的采访记。关于黑狗,我想效仿记者,对附近的人进行一次采访。
听了我的想法,何强哈哈大笑起来,他正在啃一块玉米饼,咬碎的粉末喷得满地都是,同时他被呛着了,一笑就咳嗽,还没咳完又笑,好不容易咳完笑完,他说:
“嗯嗯,是该好好采访一下。”
看他笑成那样,我以为他要反对,没想到他表现得比我更有兴趣。就算他口是心非,我也顾不上了,我迫不及待一门心思要进行采访。
“我们是站在小巷问过路的人,还是挨家挨户去采访?”我征求他的意见。
“先站在小巷问过路的人,”他说,“然后挨家挨户去采访。”
既然是采访,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总该有的。我从书包里掏出红塑料皮包装的笔记本,那是我爸刚送我的,还没有用过。我左手拿着打开的笔记本,右手握住笔举在空中,做出一副随时都要记录的样子。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从小巷那头匆匆走来,我赶紧走到路中间,何强站在一边,把手插进裤兜里,脸上似笑非笑的。
“请问,”我对来人说,“你见过一条黑色的狗吗?”
“没有。”她说。
她不打算停下来,她回答问题时仍然在走。我第一次充当记者,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不知所措,我正犹豫要不要追上前去,她已经走出了小巷。
我把两只手放下来甩了甩,那种姿势做久了难免有些发酸。
“又来一个。”何强小声说。
那是个年龄不小的男人,背上背着一个大口袋,里面的东西压弯了他的腰。我走过去弯着腰问:
“你见过一条黑色的狗吗?”
他歪着头看我一眼,走到小巷边蹲下来,后仰着把口袋放到地上,他脱出套在肩上的绳子,随后喘了一口气,我们听见他的嘴里发出类似吹口哨的声音。
“你是说一条黑色的狗吗?”他问。
“是的。”我说。
“有多黑?”
“非常黑。”
“黑到什么程度?”
“比你见过的黑狗都要黑。”
“嗯,像这样黑的狗我倒没见过。”
“好的,谢谢你。”
采访还算顺利,虽然他没有见过那条黑狗,但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照这样下去,总会访出结果的。
我们又采访了几个人,看得出他们对那条黑狗感兴趣,问题是这并不重要,他们不是本地人,而是过客,感兴趣说明他们不知道,他们越感兴趣,我们就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我和何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决定放弃在小巷的采访,按照事先的计划,上门去采访本村的人。
何强建议从王老头开始,我认为有道理,王老头是个孤寡老人,他爱串门,爱在我们面前唠叨,对当地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王老头见我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笔记本,很正式地采访他,一下来了精神。
“你们想问什么呢?”他说。
“你见过一条黑色的狗吗?”我问。
“黑色的狗有很多,”他说,“本地狗基本上都是黑色的,十条中最多有两三条长着花斑或者黄毛。这么多黑狗,你问的是哪一条?”
“是最黑的那条,”我说,“总之我还没见过比它更黑的狗。”
“是的是的,”他说,“同样是黑狗,但黑的程度不同,有的不怎么黑,只能勉强算着黑狗,有的就黑多了,像煤炭一样黑。你说的这条狗有没有煤炭黑?”
“比煤炭还黑,”我说,“至少和那些黑得发亮的煤炭一样黑。”
“你说对了,”他架起了二郎腿,“煤炭也是这样,参杂了泥巴看上去灰蒙蒙的,不够黑,也不经烧,你知道煤炭越黑质量越好。”
“这跟狗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把话题转到狗身上来。
“怎么没有关系?”他说,“我们不是在拿它跟煤炭作比较吗?那些黑得发亮的煤炭多好啊,是不是?”
显然他很愿意和我讨论煤炭的事。站在我身后的何强,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接着他转身冲出门外,我听见他在外面强压着声音笑个不停。
“老年人就是话多。”我出来说。
我们想找年轻一点的,王老头家旁边就住着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大约半年前结的婚,新娘子是外地人,长得娇娇小小,怎么看都不像是下地劳动的农民。我们见门开着,便直接走了进去。
“喂,那条最黑的狗你是什么时候看见的?”何强突然抢在我的前面说。
新郎埋着头坐在板凳上,他的面前有一些瓷碗的碎片,另外,一些不该放在地上的东西,也散落一地。我们听见里屋有女人啜泣的声音,不用说,那是娇娇小小的新娘子在哭。
“我他妈只见过最黑的人,”新郎说,“你们两个小狗日的还不滚出去!”
我们只好滚出去。我埋怨何强不该那样问人,他老练地说出一些词,我没大听明白,什么逼供诱供的,还说有的人明明知道却装着不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笔记本上的采访记录已经翻到第二页,虽然翻到了第二页,其实只有一句话——你见过一条黑色的狗吗?
每采访一个人,我就用一行写下这句话。我拿着笔记本仔细端详,单从排列来看,谁说不像一首诗呢?我正在欣赏,何强说:
“看来这些人都和我一样,没见过那条狗。”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之意,他不相信有一条这么黑的狗,他甚至怀疑我是为了采访而杜撰了这条狗。
“现在我就带你去看它。” 我说。
不巧的是,河谷对面空荡荡的,连一条狗的影子也没有。何强免不了要说风凉话,他认为大家都没有看见,就我一个人看见,有也等于没有。我满腹委屈不知该如何表达,换成后来,我肯定会辩解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在河谷对面,那条象征着真理的黑狗始终没有出现,更不要说和其他狗站成一排。而这边,倒是小飞、跛子和二崽跟我们站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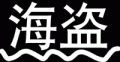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吉木狼格,男,1963年生于四川大凉山。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静悄悄的左轮》等。现居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