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树下的邓兴讨
◎ 张羞
2001年一个秋天下午,杭州的阳光特别明亮柔软,我们骑车去市电信局办理电话安装手续。我们是我和我的室友老李。一路上,我正分辨着此地的植物和别处城市的有什么不同,手机就响了。我接下电话,对方是一个低音比中音明显但没有高音的男人,他说,是张羞么。我说是的。他说,那下午过江来喝酒。我说好,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挂了电话。两个人继续不紧不慢地骑着自行车。在快要到武林广场的路口时,老李还是问了我一句:那人是谁。我说我也不清楚。后来,我不得不反拨回去追问那人的来路。没出意外,那人当然是邓兴讨。在电话里,他说:我叫邓兴。我想这下子坏了,我欠下了一个人情,准确地说应该是酒情。
那天下午,阳光的确很好,难得一见的风和日丽。我自然是没有和邓兴一起喝酒,因为他说的那条江远在我昨天刚坐长途火车离开的武汉。
所幸的是,没过两个月,我又一次去了武汉。一到武汉,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还这个酒情。我们约定在江岸上见面,因为他就住在长江边上。我不记得那天武昌的阳光如何,反正我从灰蒙蒙的汉阳坐车经过长江大桥再绕一圈来到江边上的车站时已是黄昏时间。我站在防洪堤坝上点燃一根香烟,眼前是来回穿过桥墩一排一排冒气的挖沙船,我感觉到一些凉意,但那天还没到寒冷的季节。这这里,我说到了凉意,又说到寒冷,并没有特别用意,无非是说邓兴讨,他是一个暖和之人。他不仅暖和,而且还是暖和的两倍。理由是他本身就比一般人大一倍,或者重一倍。那是在碰面之后,在此之前,我以为邓兴讨是个轻灵的人,就像他写的那些诗一样。我听到有人喊我,便回过头,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子在招手的同时正向我走来,他穿一身黑色便服,裤子也是黑的。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需要任何装饰,就可以扮演一位黑帮人物。
金龙泉,或者行吟阁,武汉的啤酒都是清爽型的,这和这所潮湿的城市完全不同,也许是我不够了解的缘故。不过,和城市相比,我了解起一个人的速度会更快,前提是我想成为那个人的朋友。啤酒是不错的催化剂,几杯下来,我们已经从城市建设聊到了半空。在半空中,有一些我们喜欢的诗歌。那是一个需要谈论诗歌的年纪,不像现在,现在只要独自去面对,然后慢慢把它们写掉。这个不说。
我要说的是,我已经2年,2年多,没有见过邓兴讨了。倒数上去最新一次见面还是在04年农历正月,他已迁移到更南方的城市,工作性质还是造船。我从北方回到武汉过年,他从南方上来喝酒。我们的酒量比以前都有所增加,也比以前敢喝,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以前喝得快了。这时候的邓兴讨已不再是一个标准胖子,他在那个造船厂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慢,也许他本身就很慢,他慢慢地喝着啤酒,慢慢地从烟盒里抽出香烟,然后慢慢地把它点燃,这让我觉得他已不再适合演黑帮角色。喝掉杯子里最后一口,他说,我现在写诗比走路还慢。说完,重新到满一杯啤酒。我没有立刻说话,让自己停了停,我知道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同样适用。那这样吧,我说,是不是你太瘦的缘故?
事实上也是如此,那天凌晨我们的出租车在江边停下,两个黑乎乎的人从车上来下,很难在马路上站着。冬天的武汉异常湿冷,但那不是我的感觉。在我游荡的日子里,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暖和还有在不熟悉地方的安全,只因为身边多了一个同样喝高了的人,而这个人恰好就叫邓兴讨。两个人无心去留意长江上的雾气,搀和着上了宾馆二楼。
至于汉阳树,那仅仅是邓兴讨在诗里想穿过江面望到的东西,我从来没在散步途中见过,可能他也没有。类似的东西还有“彼火车”和“不停从江上翻墙过来的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写它们的时候还是一个用邓兴作为笔名的胖子,可现在他变瘦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座内河上的造船厂附近找到可以喝酒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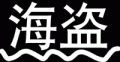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张羞,男,1979.12.3生于浙江嵊县。2001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随后开始诗歌小说的写作。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