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的病(小说)
◎ 何小竹
1
你要到哪里去?老婆问他。我要去医院,他说。你病了?老婆感到一点惊奇,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好象是,他回答说。好象?老婆冷笑了一声。什么病?她问他什么病的时候,嘴角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笑意。笑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冷。谁知道?他说,所以才去看医生嘛。他从桌子上端起一杯水,一口气喝光,就准备出门了。你是该去看一下医生了,老婆冲他背影这样说了一句。
2
医生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回答说,全身上下都不舒服。医生听他这样回答,迟疑了一下,目光在他的脸上多停留了片刻。把舌头伸出来,医生命令道。他张开嘴,伸出舌头看着医生的脸。这是一张宛如银盘的脸。五官的分布说不上漂亮,但也中规中矩,没什么缺陷。头发梳得光光的,在脑后盘成一髻,透露出医生特有的严肃。她一定是结了婚的,块头还不小,掩藏在白大褂底下的胸脯十分成熟、饱满。她的丈夫一定是个方脸盘和留着络腮胡的男人。他们一个礼拜做爱一次,或做爱两次。她中规中矩略带严肃的五官在做爱的时候会有些扭曲。比如,眉毛紧缩在一起,鼻孔(医生有着一个圆润的大鼻头和两个小巧而匀称的椭圆型鼻孔)会放大,嘴唇(医生的嘴唇质地厚实,线条圆润而精致)将微微开启。她也会在这个时候伸出舌头吗?阿——,他听见医生发出了这个颤音。阿,跟我念,阿——。医生用一支小木片压住他的舌头,示意他学她的样子,发出一个略带颤抖的“阿”音。阿——,在小木片没有任何味道的压迫和刺激下,他发出了一个明显沙哑(且有几分羞涩)的“阿”音。阿——,再来,医生命令。于是,他加大了一些气流,并按四分之四拍的节拍长度,再次发出那个“阿”音,其音高比刚才提高了二度半(最后高起来的那个半音是在快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四个节拍中的最后一拍升上去的)。医生又用冰凉的听诊器探进他的胸胸脯,戴着耳塞的表情显得全神贯注,尤其那双成熟的眼睛,看着他,像要一直看透他的心脏。做一个全面检查,既然你全身都不舒服。医生把听诊器从他胸脯上收回来,埋头开出若干张单子。医生开单子的时候问:姓名?他回答:张自。张开的张,自由的自。他自以为幽默地附加了一条解释。医生并没有发出他期望中的那种会心一笑。年龄?四十。医生停下行走如飞的圆珠笔,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你有四十?是的,他如实回答,还差几个月。看上去蛮小的,医生笑了一笑说,像是自言自语。她已经将所有的单子都开好,递给他。去吧,医生抬起头来的时候,又笑了。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笑。在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她又告诉他,一会将检验报告拿回这里来。
3
先是验血。他将右手食指伸给一位脸上有小酒窝和小雀斑的护士。但马上他又将伸出去的食指缩了回来,换成左手的食指。小护士本来已经准备接受他的右手食指,却没想到抓了一个空,显得有点气恼地瞪了他一眼。当他重新伸出的左手食指被小护士捏在手中的时候,他看见了小护士另一只手上捏着的针头。他下意识地又想缩回来。但这次却没那么容易了,小护士既然已经将他的那根犹犹豫豫的食指捏住了,当然不肯轻易松手。你这么怕痛啊?小护士一双漂亮的凤眼露出与其年龄和相貌都不太相称的威严训斥道,都成年人了,还不如一个小姑娘勇敢。他偏起脑袋看了看旁边的一个小姑娘,嗯,她是够勇敢的,血从她的小指头上渗透出来,她既没退缩,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表情还是那么沉稳。哎——哟,他突然大叫一声,再看自己被小护士捏在手中的指头,指头上冒出了殷红的血珠,小护士已经放下了手中的针头,用一块长方型的小玻璃片将血珠从指头上粘了过去。然后,拿了一支棉签压住指头上还在渗血的针眼大的小孔。自己将棉签压住,别松手。小护士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告诉他,并连同棉签一起,将他的左手食指还给了他。他用右手压住左手上的那支棉签,又看了看旁边的小姑娘。小姑娘也一直在看他。要等多久?他问小护士。过一刻钟来拿化验报告,小护士的语气比刚才缓和多了。然后查大小便。做B超和心电图。他在不同的楼层之间上上下下。有时候电梯拥挤,他不得不爬楼梯。对于用于探测他身体的任何一样仪器,他都很畏惧和反感。他也不喜欢医务人员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冷漠。幸好这一路上总有一两个漂亮的女病患可欣赏,以及想到一会还要去见那个脸若银盘的医生,才没有让你对医院这个地方厌恶到绝望的地步。
4
他把一摞报告单放到医生的面前。他看着她,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是那种带着信任与敬意的期待。他从未对任何一个女性有过这样的目光。你没病,医生说。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奈之下,她又说了一遍,检查结果,你什么病都没有。他还是不相信,怎么可能?我浑身都不舒服,没胃口,要么整夜失眠,要么成天昏昏欲睡。我对任何事情都缺少兴趣。还有……还有阳痿。他不好意思地看了医生一眼,便迅速地将目光移向别处。医生看着他,善意地笑了一笑。检查的结果就是这样,她说。也可能你确实有点什么,但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手段查不出来。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如果你还不放心,可以去看看中医,或许他们有些办法。他收回自己的病历和那一大摞报告单,比来时的神情更加沮丧地站起来同医生告别。谢谢医生,他说。等一等,她叫住了他。她犹豫的神情让他在回头的瞬间感到了一丝温暖。你干什么工作?原来她叫住他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他显得有几分失望。做点小买卖,他说。是老板?她又问。此时他沮丧到极点,以至于对这位素昧平生的女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怨恨。他就用这样的眼神看了看她,没有回答。他转过身,匆匆离开了医院。
5
这晚上他没有回家。他在大坪附近的录象厅过了一夜。
录象厅到后半夜开始放毛片。他被毛片里面的喊叫声吵醒了。他翻身从座椅上撑起上半身,像做梦一样地盯着电视机屏幕,看了半天,眼神里才流露出回到现实的迹象,原来是放的毛片。他起身去到录象厅外间,解了小便,又拍醒门口守小卖部的老头,买了一瓶矿泉水。他手里拿着那瓶矿泉水,坐在椅子上,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屏幕上的性交表演。他看录象的姿势很专著,但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不显得兴奋。他几乎就是面无表情地看着。逐渐地,他的表情中才有了一点惊异的神色。他发现,将他吵醒的喊叫声不仅来自前方的电视机,也来自他脑后的墙壁。当他发现这一点之后,基本上没做任何思考,就转过头去。他看见在最靠墙壁的那排座位上,一对男女正在做着与电视机里类似的颠簸动作。那个正在做颠簸动作的男人发现了从前排转过头来的他的目光,一下便停止了动作。而那个女的是背对着他的,并不知道前排还有人转过头来看他们,非但没停止颠簸,而且,由于身下的男人突然停止不动,使得她上下颠簸的幅度还有加大的趋势。那个与电视机遥相呼应的喊叫声,就是随着她颠簸的节奏而震荡出来的。尽管那个男人已经注意到了他回头的目光,但他却没想到马上转回头去,而是以他刚刚看电视机的表情和姿态看着他们,仿佛他们是另一个电视里的画面。你妈×!那男的终于愤怒地喊叫了一声。这一声喊叫中断了女人的喊叫。女人也停止了颠簸,回过头来,与他打了个照面。直到那个女人看着他露出奇怪的笑容,他才恍如梦醒一般,慌忙将头转过来。此时,电视机里面仍然是一片呼天抢地的喊叫。而画面上已经不止一对男女,而是一群男女,那情景完全像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
6
好不容易,繁忙的工地才沉寂下来。一对恋人穿着泳装在海滩上追逐,伴随的音乐是舒缓的,与海浪的节拍大致吻合。他再次出现困意,重新靠在椅子上睡去,直到定时的手机闹钟将他吵醒。
7
约会地点离他昨晚睡觉的录象厅不远,就在较场口旁边的一栋大楼里。他不记得是第几层了,点开手机上的记事本,查看4月4日的记事:去三友公司谈广告方案,较场口路128号附3号,向阳大厦12层B座12号。阳光很明朗,这在多雾的山城十分难得。他在楼下的摊上买了两个包子,一瓶豆奶。结果,包子吃了一个,第二个咬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他匆匆将豆奶喝光,剩下的包子扔进垃圾箱,用餐巾纸摸了摸嘴,进了大楼的电梯间。这是上班高峰,两台电梯根本不够用。他总是比较谦让,不去拥挤。每当到了最后关头他站上去的时候,电梯就发出超员的尖叫。叫归叫,进了电梯的人根本就不理睬,宁肯电梯不启动,也没人让出来。没办法,只好由他从电梯里退出来了。最后一次,他坚决不打算退了。跟他一起挤在门口的是一个胖子,他觉得胖子退出去比他这个瘦子退出去更解决问题,一个顶他三个。他的背后是一个女人,这女人也比较胖,丰满的胸脯压住他的后背。胖胖的女人一副急躁的样子,嘴上不停地唠叨,说下去几个不就行了嘛,并一个劲地用她软绵绵的胸脯在他背后冲撞,有要把他推出去的不良用心。他假装感觉不到,稳住身子,面无表情。这样一来,倒也没有人敢指明道姓把他哄出去。他的样子天生就长得不讨喜,眉毛倒立,眼睛还是单眼皮,鼻梁像刀片那样架在脸上,薄薄的嘴唇还不能完全包住他已经被烟熏得半黑的牙齿。幸好他还戴了一副眼镜,使他看上去还有几分像个知识分子。要是把眼镜去掉,说他像个杀手也不算十分夸张。这也是他能坚持住不下去的一个外在的因素。另外,在心理上他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支撑的理由。我是病人,昨天还去了医院,我很虚弱,我本来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而不应该我去照顾别人。况且,我已经主动让出了几次机会,这次我要把机会留给自己,我不能也不应该再让出去了。他一脸冷漠的表情正好对着胖子的一脸横肉。胖子一双鼓凸的眼睛一直在和他戴了800度近视眼镜的眼睛对视。开始他也无所谓,看就看吧,你敢把我怎么样。但渐渐地,他的眼睛就不行了,像是起了雾的那种感觉。他心里一慌,看来不仅块头不敌这个胖子,就是瞪眼睛也是瞪不过他的。正这样想的时候,胖子抓住他的胸口,一把将他从电梯里拽了出去。
8
他站在电梯口,看着电梯关上。他看见电梯里的人都在冲着他笑。他也笑了笑,还莫名其妙地朝他们挥了挥手。他穿了一件灰白色的皱巴巴的灯心绒西便装,一条牛仔裤。他的头发浓密,坚硬。但就是显得有点蓬乱,有点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的那个样子。他抄着手看电梯门边上的楼层显示器。还有几个人也围在他旁边,也抄着手,盯住那个显示器看。2、4、6、8······21。显示器上的数字停滞不动了。电梯在21这个数字上挂了大约一刻钟,数字便开始往下滑动。19、17、15、13、·····1。停顿了约三秒钟,电梯门缓慢地打开。电梯里的人群鱼贯而出。接着,电梯外面的人拥进电梯。这次,他站到了电梯的最里面。电梯没有发出尖叫,而是顺利地关上门,启动,向上提升。他有点失望。他觉得奇怪,电梯里的人数和前几次差不多,也是挤满了的。但前几次都尖叫了,这次却不尖叫。他迫不及待地挤到电梯的最里面,这自以为聪明的行为却被证明完全是多余的。12,电梯晃了一下,停下来,门开了。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电梯的门已经关上。13、14······电梯继续向上提升。他皱了一下眉头,索性安下心来,自暴自弃地随电梯上到最顶层。
9
随他一同上到顶层的就剩下两个。他们是一男一女,都比较年轻,相互依偎的亲密动作看上去像是一对恋人。为什么是恋人而不是夫妻呢?他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在心里暗自一笑。就在电梯还在往上提升的时候,那个女的还仰着头用嘴唇在男的那个有点胡须的下巴上蹭来蹭去的,完全就没把他的存在当回事。当然,他也没避讳。他就看着那个女的在男的身上蹭。而且他发现,那女的其实并不漂亮,还可以说有点丑。男的在长相上倒是没什么特别可挑剔的地方,就是眼神(感觉自己正在为爱情而沉醉的那种眼神)显得比较平庸,可猜想出平常是个不大动脑筋的人,品质不坏,但也不像有幽默感的人。正当他准备进一步去猜想这男孩的职业的时候,电梯已经到了顶层。女孩用自己的嘴唇迅速地在男孩的嘴唇上做了最后一次亲吻,便双双出了电梯。他们出电梯的时候,身子都还是粘在一起的。然后,上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进了电梯,将手按住电梯操纵按钮的停止键,侧过头看着他。他也看着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也可能她还在等什么人?他于是又看了看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女人终于忍不住,问他,你不下吗?用的是极有礼貌的普通话发音。这是一个穿着和举止都十分优雅的中年女人。他马上明白过来,说,我要下,但不是下电梯,我到12层。说着,他朝女人那边靠了靠,伸出指头在12这个按键上去点了一下。我刚才坐过头了,他退回到原来的站的位置。可能是听到他一口气做了这么多的解释,女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含义不明的微笑。然后,她没有再看她,而是侧过头去,看着别处。他也不看她,也看着别处。但这样看了一会,总觉得有点不自然。他于是又看了她一眼。刚好,她也在此时回头,目光相遇在一起。他心一慌,把头偏了过去。但马上他就有些后悔,为什么是我要先躲开她的目光,而不是她躲开我的目光呢?电梯分别在19层、17层都停了一下。门打开了,却不见有人进来。也许是谁按了外面的按键之后又离开了。电梯门无声地自动关上,继续往下坠落。这意味着,如果一路上都没有人要进电梯,或者,她不在中途下电梯的话(基本上她不会了,她按的是1层),那么,他和她就要这样孤男寡女相伴到第12层。他又看了她一眼,这次她没有侧过头来用目光与他交接。他于是得寸进尺,将目光固定在她身上,决意就这样固定坐,不拿开了。而中年女人呢,也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爱看就看吧。她应该是阅历很丰富,内心很成熟的那种女人了,应付这样的场面已经很有经验,不会流露出那种小女生的脸红心跳。她还在中途很从容(当然也是不失优雅地)用手指梳理过几次垂在耳鬓的头发。其实她的头发并没有乱,电梯里的小排风善还不足以吹乱她的头发。这不过是习惯动作而已。但也未必不是想掩饰一下内心的什么。她上身是一件浅灰色的两件套时装,下身包裹在一条大面花的长裙里。长裙的下摆露出一双米黄色的高跟鞋。她是侧对着他的。所以,应该说她无意中(或是出于不想要正面对着他的无奈)而将自己的身体曲线以最佳的角度展露给他了。
10
但就在电梯到达13层的时候,她出乎意料地偏过头来,与他的目光相对。他本想坚持住,坚持到对方不再坚持的时候。但是,她的眼睛(一双阅人无数且带有一点儿风尘味的美丽的眼睛)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看透了一切的神态让他感到了几分心虚。她看透了他什么呢?幸好电梯很快就到了12层,他慌忙收起目光,匆匆地出了电梯。
11
张自,你搞什么名堂嘛!他刚出电梯,过道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穿着一双笨重的靴子怒气冲冲地跑过来,向他又是跺脚又是瞪眼地训斥。看看都几点了?她的怀里抱着一只沉甸甸的资料袋,背上还背了一只苹果牌旅行包。她继续以训斥的口气对他说,人家卢总都把我骂惨了,说就凭你们公司当头的都是这个样子,毫无时间观念,公司管理不晓得有多混乱,哪个还敢拿业务给你们做?他几乎是被她拽着往写字间里走,好不容易顺出一只手来,以一种父亲爱抚女儿的动作,慈爱地在她的头发上抹了一下。讨厌,女孩生气地挥了挥手臂。我看你怎样向人家卢总解释?她用那双画了蓝眼圈的眼睛朝他撒娇似地恨了一眼。他这次没有去摸她的头发,而是鼻子冲着前方轻轻地哼了一声,球莫名堂。
12
总经理办公室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一圈人。唯一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着的是一个胖胖的长了一张娃娃脸的秃顶男人。他正在埋头看一份资料。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同时也抬起手来,摘下了鼻梁上的一副眼镜,捏在手上,以舒缓的节奏,敲击着腿上那本打开的资料夹。卢总好,张自冲他点了点头。他还想说点什么,便看见卢总按了按手,示意他坐下。他朝身后看了一眼,沙发上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但沙发的旁边还有一张单人皮椅。他就在这张单人皮椅上坐了下去。小辉,你也坐。卢总用他捏着眼镜的那只手朝那女孩晃了一下。坐卢总旁边的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马上站了起来,将座位让给了女孩。女孩乖巧地先是露出一丝笑容,然后又说了一声谢谢,就在卢总的旁边坐了下来。咳咳咳……嗯,在场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清理了一下自己的喉咙。
13
OK,我们开始吧?卢总说道。
14
检查出来了吗,什么病?老婆问道。没什么病,他说。西医说我没什么病,但我还想去看看中医。老婆就笑了一下,你是一定要检查出一个什么病来才满意吗?他想了想,很郑重地告诉她,我是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劲,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希望你能同情我,把我当成一个病人。老婆说,你那么紧张干吗?你干你的,我管过你吗?他看着她,不说话。老婆又说,好了,别做出一副疲惫不堪可怜西西的样子,想睡就去睡了吧,我也困了。去吧去吧,看不来你那副样子。
15
张自如释重负地进了隔壁自己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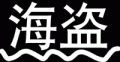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何小竹,男,1963年生。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6个动词,或苹果》,小说集《女巫制造者》及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等。现居成都,为居家写作的自由职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