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我的没有实现
◎ 赵猪
1999年的秋天,我以为我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交一个女朋友,但是很快,阿勇的出现改变了我的想法。
第一次见到阿勇的时候,他对我很不以为然,我对他也并不是太感冒。
我当时是个楞头楞脑的学生。我已经不太能回忆起当年我的样子了。但是肯定不是我现在的样子,大圆脸,双下巴,因为吃槟榔吃的,两个腮帮子已经鼓了起来。满脸横肉,好象屠夫一样吓人。或者我当时还稍微青涩一点吧?也或者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这样了。阿勇倒是一直没变过,鹰钩鼻子,惨白而又油腻的脸,脏乱的长头发。
当时我是想去找个老板免费提供演出场地给盘古的,结果老板找来阿勇跟我谈,好象还有一个做主持人的家伙吧?我对那人印象不是很深了。然后我告诉阿勇是做盘古的演出以后,阿勇的眼睛亮了一下,我知道,事情成了。
在赶往长沙的火车上,阿勇和要要找到了我,我们窝在火车连接处抽着香烟,大声地谈笑着,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从那以后,只要我们在一起坐火车,肯定第一时间抢占这个地方,即使有位置,我们也要抢这个地方,搞得自己脏兮兮的,但是笑得却总是很开心。
1999年的十月,我做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出,我的身份应该算是经纪人吧,喝了一大堆酒,认识了一大群人,害得一个老板亏了好几千块。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一支乐队。
1994年的时候,在我谈我很要命的初恋的时候,我就对那个有着一对大眼睛的文艺姑娘说了,我一定要做一支伟大的摇滚乐队。其实那时候,我只知道唐朝而已。然后这个梦,随着我与她的分手,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了,只是一直到1999年的秋天,梦才有了它真正可以实现的契机。
阿勇的乐队那时候已经有四个人了,很标准的配置。而我们经常在聊天中说到互相认识的朋友,郴州就是那么小的,一说一说,大家的朋友圈就有了交集,大家的关系也就近了很多。但是对于一支平均年龄在25岁以上的乐队,要相信我这样一个不过22,什么乐器也不会的家伙,很困难。
阿勇和要要都是从资兴过来的,两个鼓手,所以要要只能做主唱了。他长得很清秀,起码比阿勇好看,而且他很喜欢照顾人,洗啊涮啊,煮啊炒的,都很里手。张华年纪最小,比我只大一岁,贝司手,据说他的技术很好,但是我也不懂。他们的乐队叫手,我一直在想,一只手是需要五个手指头的,所以,加上我最合适了。赖四平原来是个画家,后来学了吉他,技术也很好,反正我听不出问题来。
手乐队的演出热情,排练热情,随着我的到来,越来越高涨起来了,他们在排练,也开始上班了。忘记说了,他们一直都是在做着夜总会伴奏乐队,过着颠倒的生活,而我当时不太认真地在当地的一个大学里读书。除了排练,上班,读书之外,我们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凑在一起闲聊,发神经,听歌,扯一些不着边际又好象显得很高深的卵谈。或者就跑到我们学校的食堂里去吃饭,有时候是两个人,有时候三个人,要不四个人。赖四平很懒,张华已经有老婆了,阿勇也有老婆,但是他老是一个人跑出来玩。我们买一瓶绵竹大曲,打几块钱菜饭,就坐在食堂的座位上边喝边聊,我的酒量一直不错,那时候尤其好,一中午喝下去,大家就都晕了,然后我们就爬墙爬到学校隔壁的苏仙岭公园去玩,每次最多也就走到半山腰,就不会再往上爬了,因为我们都很懒,也没什么体力。忘记说了,我老是忘记说一些事情,很麻烦。我们这的习惯,住在一起的女朋友就是叫老婆,其实未必打了结婚证,反正现在公安局查这些查得也不是很严格。
那时候老跟我们来往的还有一支邵阳的乐队,叫拆,是王志超、邓卫松弄的乐队。他们在冬天里来过一次。那时候,手乐队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排练室了,就在火车站旁的一个废弃歌舞厅里,我经常跑到那去玩,他们的老婆也经常过来。张华的老婆最烦躁了,总是拿着一堆毛线在那打毛衣,不知道是给谁打,就是不停地打,也不管他们弄出来的音乐多激烈,多雄燥。然后阿勇就更烦躁了,他觉得谁听了这些音乐要么就得受不了,要么就得投入进去,但是张华老婆的冷静让他忍受不了,为这个事,他跟张华已经吵了不只一次了。
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是那个冬天最暖和的地方,在南方阴暗潮湿的天气里,是我最温暖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刚因为考试舞弊以及和监考老师打架被逼留级。必须要留到下一个学年去,跟比我小上两三岁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然后我就天天地呆在这个房子里,乱喊乱叫,反正他们也只是要排练,并没有具体地要排出什么东西来。
拆乐队录了一张小样,呆了几天就走了,他们喜欢阿勇打的鼓,说阿勇的技术好,我看过的不多,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好到了什么程度。相反,我还经常笑话,我们都经常笑话阿勇现在的体力很糟糕了,越来越瘦,而他老婆的身材却越来越丰满了。这估计就是阿勇把养分都给了她,所以我们都劝阿勇晚上要惜力一点了,不要太勤快,阿勇一般都不理我们,然后实在急了,就大家摔交玩咯,反正那间房子里还有些破烂的地毯,倒在地上也不脏,也不疼。
具体的事件我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每天都差不多,没什么必须要被记住的吧?我跟他们越来越熟了,但是做乐队,还是不可能,他们不信任我,我什么都不会,不可能被人信任。我说,我可以做一个人声乐器,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前卫,我们受很多的音乐杂志影响,总想把音乐做得乱七八糟,与众不同。但是他们不能接受,也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都比我大。
所以我开始学乐器了,先是跟阿勇学打鼓,天天拿着一对阿勇送我的鼓棍到处乱敲,妈妈很不屑地看看我,也不管我每天把自己的枕头打得又扁又平。我还去跟学校里的人一起搞乐队,演出,结果排练完几场以后,那个吉他手拐了我几盘磁带就跑了,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你打鼓很有感觉,很生猛。但是在演出的时候,他找了个学打鼓但是没感觉的女孩子上台。
还有一帮小孩子,他们在跟着阿勇他们混,我也想拐骗他们跟我组乐队,可是别人的乐队也是成型的乐队,什么都有,我没有位置可以硬加进去。
我想谈恋爱了,我突然地想谈恋爱了,谈上恋爱以后,我就没那么多功夫去跟他们瞎混了,我就不至于老是在郴州那几条小街上逛来逛去,什么事也不做了。说不定等到毕业,我的恋爱就谈成了,然后找个工作,我就可以结婚了,再过上几年就能生孩子了。我觉得我做乐队的梦已经破灭了。
手乐队演出了好几场,并没有什么反响,赖四平的吉他还是在往老套路上走着,一点都不好玩。我一直跟着他们到处跑,做个跟屁虫。背琴,喝酒,闲聊,我觉得很神气,但是也很没劲,因为演出的时候,我只能站在台下。我想我做摇滚明星的梦还没有破灭。
其实我的本事只在写点文字上,那时候我认识了彭洪武,他在通俗歌曲做编辑,老让我写稿子,我就俨然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存在了。但是,赖四平最讨厌这种指手画脚的评论者,我很在乎他的看法,老是跟他争论,又总是争不过他。
他们都有很多女朋友,都有,只有我没有,我总是叫他们介绍女的给我认识,我当时还是个处男,我想摆脱这个身份很多年了,但是他们介绍过之后,也没有一点用,我还是一个人到处走来走去,好烦躁的。
赖四平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了,他老婆长得好漂亮,比他还大两岁,我看过他女儿和他老婆,还在一起吃过饭。我开玩笑,对赖说,干脆把你家女儿就定给我算了,赖四平开始不置可否,到后来我提得实在太多,玩笑实在开得太过分了,他就来揍我,我就跑。我知道不可能,开个玩笑而已,但是我始终把握不好玩笑的分寸,大概,我认为,赖四平最后会跟他老婆复婚的,又忘记说了,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再过上几年,或许赖是会跟他老婆复婚的吧?如果是我,我就会。
张华也准备结婚了,他老婆又打了一胎,那个姑娘没工作,就是天天打毛线,跟着张华,张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得上了糖尿病。生活变得乱七八糟了。
有一天,他们说,他们准备去江苏跑场子了,那边有一个夜总会叫他们一起过去,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我当时很失望,好象那段时间我总是逼他们请客喝酒吧。那时候是夏天,深更半夜地坐在大街上喝酒,我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最后都变成了呕吐,喝多了啤酒,肚子涨得难受,拉尿拉不完,就只好全都吐了出来。
我准备把我的心思全部花在那帮还在学乐器的资兴的小孩子身上,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懂,听得也不多,乐器也不是太厉害,只是几个人坚持着住在郴州做乐队而已。但是最让人烦躁的是,他们换过的女朋友也都一个接着一个,而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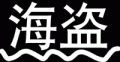 ┩目录┡
|